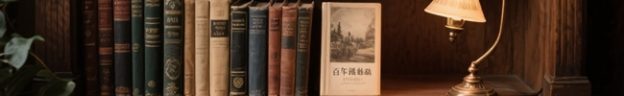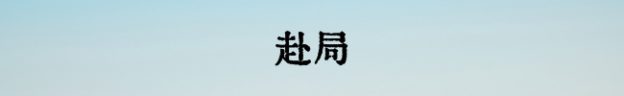早上做完家务,在阳台休息,刷到吴彦祖卖英语课,他说:“Hey friends,I’m 50 years old.But i truly believe this is the perfect age to keep going for it.”百词斩我已经斩到第125天;多邻国一周刷到白银等级,连续一周榜首。也不知道这把年纪了英语学来做什么。每天就这样什么都不图的学,看看能继续到什么时候。之所以没用“坚持”这个词,是因为我没觉得这是在坚持。
取快递时和小区里唯一的菜鸟驿站的老板聊天。
老板左右手都各有两个大拇指,两手共有十二个手指,头发花白。
她说这菜鸟驿站在这小区,两年里上上下下搬了三次。最早时每月5000元租了两间门面兼做便利店,能赚几千元。后来旁边开了一家连锁便利店,货品更多,装修更规范和上档次,于是便利店的生意一落千丈,就退了两间另租了一间更便宜的,租金只要2000元出头。由于每天的快递包裹从两年前最多时的500多个下降到现在只有300多个,只好在今年又退掉那间门面,现在这个门面月租1500元。
我说大家都能不买的东西都不买了,这两年都在熬。
90%的门店都倒闭了,连粉面店也做不下去,记忆里,2008年金融风暴也没有这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