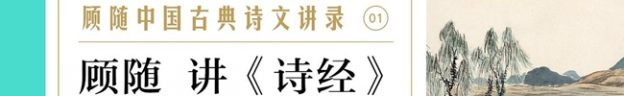读金性尧和顾随讲的《诗经》,觉得两个人的学问相比,真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金性尧在《闲坐说诗经》中说的是知识,现在AI可以整理得比他好,因为大多是罗列,少有生发;而顾随讲《诗经》,“儒释道兼融,每每一己之体悟于诗生发精妙见解”,读来不但有考据,更见人情味,不愧是“一位正直的诗人,而同时又是一位深邃的学者,一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周汝昌语)。兹录数段,以为记——
吾辈格物致知所为何来?原是为的求做人的学问。学问虽可由知识中得到,却万万并非学问就是知识。学问是自己真正的受用,无论举止进退、一言一笑,都是见真正学问的地方。做人处世的学问也就是感情与理智的调和。“诗三百篇”含义所在,也不外呼“情操”二字。情操虽然说不得“发乎情止乎礼义”,也要“发而皆中节”。情操完全不是纵情,“纵”是任马由缰,“操”是六辔在手。
吾人读诗只解字面固然不可,而要千载之下的人能体会千载而上之人的诗心。然而这也还不够,必须要从此中有生发。天下万事如果没有生发早已经灭亡。吾人读了古人的诗,仅能了解古人的诗心又管什么事?必须有生发,才得发挥而光大之。
不了解古人诗辜负古人,只了解古人诗辜负自己,必要在了解之后还有一番生发。
花月山水,人见之而有感,此花月山水之伟大也。各人所得非本来之花月山水,而各自为各自胸中之花月山水,皆非亦皆是。禅家譬喻谓“盲人摸象”,触象脚耳者说象似蒲扇,触象腿者说象似圆柱,触象尾者说象是扫帚。如说彼俱不是,不如说彼皆是,盖各得其一体,并未离去也。是故,见其一体即为得矣,不必说一定是什么。
诗人作诗皆要知其有不得已者也。“不得已”,不为威胁利诱;“不得已”,是内心的需要,如饥思食,如渴思饮。必须内心有所需求,才能写出真的诗来,不论其形式是诗与否。
《顾随讲<诗经>》,叶嘉莹、刘在昭笔记,高献红、顾之京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顾随中国古典诗文讲录”之一种,2018年9月1版,2019年12月4印。总阅读量第1607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