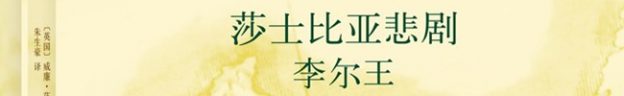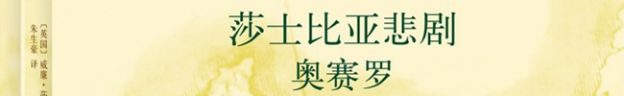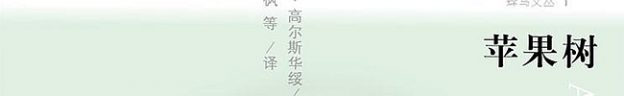李尔:一条得势的狗,也可以使人唯命是从。
早上和太座散步,年初二,一个人都没有遇到,只有梅花安安静静香,太座说真是岁月静好。我说多数人都被“你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这句话洗过脑,但我不认同,因为我们自己的担子,是我们自己在挑;我们自己的岁月,是我们自己在过。“是的,我们各自尽力过好自己就好了。”太座说。
和“岁月静好”这句话相似的还有一句蜘蛛侠的叔叔临终前对蜘蛛侠说的“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我也不认同。这句话除了有道德绑架的意味在里面,还将权力和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影响力等同于个人的“能力”,这才有了现在这个世界不过是个“草台班子”的感觉——条条大路通罗马,很多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罗马梦”,可是有的人生下来就在“罗马”。“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好像你强你就要保护我,为什么?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不需要谁来帮我决定和承担。我相信的话是:影响力越大,造成的破坏就会越大。例如李尔王。
老糊涂的,至少在《李尔王》中没有什么过人的能力的,作为一个家长都显平庸的李尔在退位时,将国土分为三部分,依据三个女儿对他的“爱”的表达来分配。大女儿戈纳瑞和二女儿里甘极尽谄媚之能事,获得了封地;小女儿科迪莉亚拒绝虚伪奉承,“我是个笨拙的人,不会把我的心涌上我的嘴里;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诚实的话激怒了李尔,导致小女儿被剥夺了继承权。
科迪莉亚在随法兰西王离开前的这一段尤其精彩:陛下,我只是因为缺少娓娓动人的口才,不会讲一些违心的话语,凡是我心里想到的事情,我总不愿在没有把它实行以前就放在嘴里宣扬。要是您因此而恼我,我必须请求您让世人知道,我所以失去您的欢心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丑恶的污点、淫邪的行动,或是不名誉的举止;只是因为我缺少像人家那样的一双献媚求恩的眼睛,一条我所认为可耻的善于逢迎的舌头。虽然没有了这些,使我不能再受您的宠爱,可是唯其如此,却使我格外尊重我自己的人格。
大女儿戈纳瑞和二女儿里甘在得到封地后就羞辱李尔,并最终将他逐出家门,流落荒野。科迪莉亚率军救父,短暂团圆,但战败被俘,最终被杀害。李尔王怀抱小女儿尸体,在极度悲痛中死去。而戈纳瑞和里甘因争夺权势和对格洛斯特的私生子埃德蒙的爱慕而反目成仇。戈纳瑞因嫉妒毒杀了里甘,丈夫奥本尼公爵识破她的阴谋,她最终选择自杀。李尔的昏聩导致家破人亡,也让王国陷入战乱。这也是同样因自己的愚蠢而被里甘指使的康沃尔公爵挖去了双眼,在荒野中与李尔相遇后的大臣格洛斯特说的:“疯子带着瞎子走路,本来是这时代的一般病态。”当下又何尝不是?
下午坐地铁去青云市集送货。一路人看到的本地人,歪瓜裂枣,大声武气为了一点小事就互相指责,人人都是一副自以为是的“乡土绅士”派头;在青云市集的外地人和看起来体面一点的人,也是庸庸碌碌,一脸麻木,也就是衣着打扮“体面”一点而已。我一路上遇到的不下三五百人,没有一个大人的眼里有光,脸上有神。越来越觉得,这个社会,99.9999999%的人类都是蠢货。他们取得的所谓成就,不过是时代使他们正好在那个位置。好可怜,好可悲。稍微有点自我意识,能分辨是非,能独立思考,知道自己为什么和要什么生活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这个世界真的是个草台班子,还是这个草台班子后面其实有一群极少数的人在把控这个世界?他们就像——饲养员?这迎面走来的不是一个一个的人,全是一群一群的猪马牛羊——或者蝼蚁。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不想被圈养,也不想去圈养谁,我只是我自己。“与其被人在表面上恭维而背地里鄙弃,那么还是像这样自己知道为举世所不容的好。一个最困苦、最微贱、最为命运所屈辱的人,可以永远抱着期冀而无所畏惧。”(《李尔王》第四幕第一场埃德加)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李尔王》,译林出版社2013年11月1版,2016年8月6印。2026年第18本,总阅读量第1633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