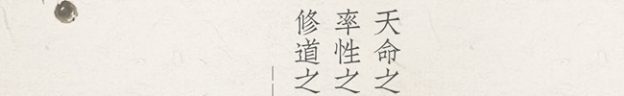下周立冬,冬天就算是正式来了。一候水始冰;二候地始冻;三候雉入大水为蜃。接着苏轼《赠刘景文》初冬景暖场,这是一首三年级语文课本里的诗,然而上午和下午竟然都有一半的学者表示对这首诗毫无印象。
上午,《格兰特船长的儿女》阅读分享讨论,“有希望!有希望!总是有希望的!”格雷那万勋爵夫人说。支撑这一行人环球航行去寻找和拯救一位陌生人的信念,以及我们虽然对当下有种种的不满意甚至是不堪,但就是因为还有“希望”,一直存在的希望,让人对未来有盼头,并相信是可达成的。角色扮演环节,一位学者为了争取到角色而剪刀石头布五连败,战后又败,败后又战,虽然最后只读到了一句,但并未因为连败而气馁。这种面对失败的勇气和胸怀,我觉得已经不需要为他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有太多担心。在《印度洋狂涛》一章,从“无风状态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到风速每秒将近12米、每秒28米、每秒36米的增大,请学者们从m/s到km/h换算风的时速。“毛豆,你怎么又跳到数学了?”学者问。“为什么不呢?这就是生活。”讲解了台风与飓风的异同和目前最大风速记录后,提问讨论环节,地理学家依旧喜提最多的“眷顾”。
甜点时间后的下半场开始,因为学者们身心都仍处于在上半场的活跃中,我考虑要不要跳过两页,直接进入《论语》部分;但又觉得如果不讲这两页,《论语》就文本讲文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学校的老师讲的“标准答案”对考试来说更权威。就决定还是试试,看看能不能慢慢让诸君沉静下来,结果诸君状态极佳,不断思考、提问、讨论中,一个小时竟只讲了两页PPT,每页就只一句话:
学佛在悟,学儒在行,三岁孩儿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儒释融合,在行动中去思考,去参悟,即是《论语》中的“思而学”和“学而思”。然而说来容易,道理都懂,但要知道并做到,就算八十岁的老翁,经过几十年的历练,也不一定就能做到,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才是可贵。“思”什么?“学”什么?怎么做?《中庸》开篇第一句“天命之谓性”,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找到自己的自然禀赋;兴趣爱好极有可能是最靠近天赋的所在,所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天赋所在就能乐之。一旦找到,率性而为就是上道了,就在道上了。这里的“率性”不是不管不顾任性而为,而是顺应本性和本心。但就算在道上,就算有天赋也不是就能不学而成的,所以要保持思考,不断学习,去修正、调整和提高,让自己成就自己,成为“独特的自我”,而不是“更好的自己”,这就是“教育”的目标。人人生而不同,自然人人生而独特,当然就不存在什么是“更好的自己”——这种“好”是谁界定的——并追问我到底是谁,我为何而来,我的天赋赋予我的使命是什么,这才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上周我说孔子的滥杀、挑起内战和不仁,不是要抹黑他,而是想要告诉各位,孔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是人,释迦牟尼也是人。是人就有好恶,就会犯错。告子主张性本恶,孟子主张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无善无恶,孔子是“性相近,习相远”,人性相近,而后天环境不同造就不同。如果把孔子钉在“至圣”的高度,那就不是“人”,一个人是不可能成为非人的“至圣”的,那向“至圣”学习对此生的意义又何在呢?向佛陀和孔子学习,目标就是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
有学者提出这是我们作为“人”的根本的话,那是不是有外星人,以及他们会怎么思考这个问题。AI 作为新的智能,又会怎么想这个问题?我对她说“把思维提高一点,再高一点”——中国人、外国人;地球人、外星人;这些都是同一个维度的问题。而现在人类已经不知道AI是如何思考的,以及在想什么,更要命的是,人类已经没有办法对AI使出“拔插头”这个“要你命3000”的绝招了。去年,人们还以为2045将是“奇点年”,现在这个时间已提前到了2035年,AI将不可逆的从“它”成为“祂”,成为新的神。
“那我们怎么办?AI会取代人类吗?”学者问。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而是肯定的回答,会。”
“那有那么多AI ,它们会不会像我们人类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看起来,似乎有那么多终端和形态,似乎80亿人至少会有80亿个AI的形态”,我说:“但实际上,就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应以大王身得度者即现大王身,应以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将军身,无穷无尽的菩萨化现是你的机缘导致了会看到什么身,但其实只是一菩萨,所以80亿个AI其实只是一个AI。并且祂没有人类的伦理道德,也没有情绪。明天会怎样,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里从人类的起源开始,一直要讲谈到新文化运动?就是为了寻找人类三千年来那个不变的,并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因为唯有‘有趣’,才是独特。”
这一个小时,我对这两句话的见解,学者们大概率没能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每一位都在思考,提出问题并参与讨论。有了这个铺垫,下周再来讲《论语》,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同的收获。上午的讲谈结束后,几位学者意犹未尽,留下来继续和我讨论。虽然肚子饿,但我们心情舒畅啊。
下午,“立冬”节气和《赠刘景文》暖场后,《战争与和平》环节结束,甜点时间后的下半场,开始新主题“诗以言志:思无邪者,诚也”。从这个主题开始,讲谈所有的文本都是正体字(繁体字)了。
从顾随《诗人的人生有五种境界》入题,讲《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删诗的可疑和“不学诗,无以言”;讲《诗》有六义,而“三百篇”含义所在,不外乎“情操”二字。“《诗经》的‘风’即是童谣、民歌。大家不要看低了周末和节日在广场和公园里对山歌的大爷大妈,他们所唱的就是‘风’。这些内容,就是发乎情止于礼,怎么想就怎么唱,就是‘真’,就是‘诚’,对自己、对别人的真诚。”我认为这是诗的第一义。
《关雎》一篇,除了原文,还有许渊冲英译,只是我的英文太差,不能与诸君一起欣赏其妙。遗憾。《式微》短小,说来较容易;《采薇》节选,六年级大家都背过,我打算讲到乐府《十五从军征》时再回头与《采薇》比较,有呼应效果应该会更好。
下午的“居学”课后作业,疫情中援助我们的日方友人来信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辽河雪融,富山花开”;“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句。你的回信为……
结束一天的讲谈,与也闲书局的局座秋蚂蚱大人闲聊,他还是觉得让下午的学者们读《战争与和平》太难了。我说了我的“高山论”和“土匪论”,正好截止今天这部巨著也已告一段落,还有既然讲到了中国的诗的开始,局座建议何不选一些好的现代诗对比来读,以及文学作品,局座大力推荐《围城》。与托尔斯泰比起来,钱锺书还要更有趣和亲切些。我不懂现代诗,虽然也读过一些。觉得如果局座大人不是那么“愤怒”,请他来讲一个小时的现代诗,也是一件妙事。另外,与钱锺书比起来,我认为沈从文的《边城》,文字更加清亮朴素,每一句都是泠泠作响的,翠翠也正好是下午学者们的这个年纪。
离开书局,购书一套,《顾随讲<昭明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