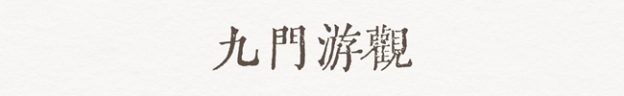沈从文《边城》的欣赏和讨论,除了我们,还有家长加入。一个小时里有大俗到大雅的转变,有“原来如此”的感叹,有人性的无奈和宗法社会里强大道德力量的感慨,当然也有每次都少不了的我和局座大人秋蚂蚱的分歧,还有对“高考体”不是“写作”,只是应试作文的共识。这三季讲谈里,曾有近十位陌生人添加我,说自己喜欢读书,想加入这个“读书会”。当然欢迎。但他们迟迟都没有现身。
甜点时间过后开始新主题,主题十三“兼爱非攻:四门游观的太子、被流放的历史之父、出身农民的东方巨子,佛陀、希罗多德与墨子”。
印度半岛的悉达多太子,小亚细亚的希罗多德,黄河流域的墨子,几乎是同时期出现。
锦衣玉食不知人间疾苦的悉达多太子有次离开王宫,从东、南、西三门出游时,分别见到老、病、死的苦难相,直观体悟人生无常;北门遇见沙门后萌生出家之志,以寻求解脱之道。那时的印度半岛也是“百家争鸣”,各种学说并存。悉达多太子出家后,四处参访苦行,但都不能了脱生死,最后在菩提树下说不证菩提,不起此座,终于开悟成佛。所以佛不是神,而是人,觉悟了的人。
希罗多德写《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如果一切皆是偶然,而人类的消亡是必要,将“历史”记录下来的意义何在?提出一个问题,埋了一粒种子。
诸子百家,“非儒即墨”,儒、墨两家占了多数。墨家快速崛起又迅速消亡的原因何在?
在先秦乱世,各家都希望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础,儒家靠的是礼,法家靠的是法,而墨家靠的是人。
墨子的“墨”应该不是姓,因为那时只有贵族才配有姓,有一个说法是有可能他长时间在外劳作、奔忙,皮肤很黑,所以称“墨”。钜子,亦作“巨子”,是先秦墨家学派对其最高领袖的称谓。墨者尊钜子为圣人,其选拔采取代际传承制度,拥有对墨者的绝对指挥权和生杀大权,同时钜子自身亦须严格遵守墨家纪律。墨者出仕需践行墨家道义,收入须捐献共享,违反者将被钜子罢免。
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却没有根基,完全靠人来推动和实现。问题就出在这里,墨家不只是一个学派,还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在这个组织里一旦一个人掌握了绝对的权利,就会直接导致独裁。
关于如何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假设了国家决策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君主一定是圣明的。但这个假设一开始就靠不住。于是墨子又为它做了解释,天子圣明是因为“天子之视听也神”。他能够无所不知是因为“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也就是天子的眼线耳目无处不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人人自危、信任崩塌,人人都是特务,互相监视、告发,岂不可怕?!所以墨家的天下秩序,听起来很美,但没有哪个君主会去做、做得到。“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凭什么?!
今天的居学,请学者们像两千五百年前的悉达多一样去游观。只是太子当年游观四门,而老贵阳有九门,所以学者们要“九门游观”——
收起手机,摘下耳机,去观察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他或她是什么髪型和长相、穿什么样的衣服、在做什么、看上去他或她快乐吗、可能是什么性格、可能正在经历什么、可能会有怎样的未来……然后站在镜子前观察自己,问自己:我和他们有没有什么不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下午讲谈结束,和一位旁听了上午的讲谈,参与了下午讲谈的家长闲聊,说也不知道这一天天的能有几位学者知道每周来讲谈的意义何在,又有几人从这里有多少收获。最后,只能说随缘罢,功成不必在我,而我必功不唐捐。
一天的讲谈结束,离开也闲书局时8元淘得旧书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杰克·凯鲁亚克《垮掉的一代》。上次读《在路上》和这本书是在2009年,一转眼16年了,家里那本早已不知去向。
回家地铁上,翻李辛的《儿童健康讲记》,“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有些书是一定要读的;有些菜是一定要尝的;有些运动是一定要做的;有些艺术是要去欣赏的;有些好玩的东西是一定要玩的;有些人是一定要见的。因为这些活动能够拓展、治疗我们的身心,在不知不觉中滋养我们。”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