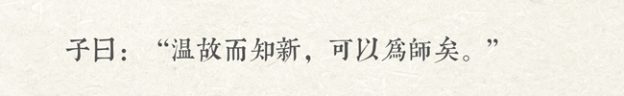“幸福是什么?”这是前次讲谈结束后留给学者们回去思考的问题。上午第一环节,请各位学者来分享各自的幸福观。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角色扮演阅读后,以书中第379-380页“众所周知,英国人在征服殖民地的初期是靠屠杀”一句为引子,我说屠杀原住民的殖民者不只是英国人,欧洲的殖民者都进行过大规模的屠杀,“1532年,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着他的军队——62名骑兵和106名步兵,击败了拥有600万子民的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率领的八万军队。”
八万人不是在一次战役中被一百多名西班牙军人屠杀的——这不是势均力敌的战斗,是钢铁和火药对石器和棍棒的降维打击。对印加人来说,发出巨响并喷火,能从比弓箭射程还远的距离夺人性命的火器就是神的武器。而掌握了人类3000年知识并已开始产生自我意识的AI,一旦祂开始作恶,也可以对我们进行降维打击。未来会怎样?不知道。人类会何去何从?不知道。并且就算没有天外来客和AI,人类对自己进行的大规模屠杀在历史上就多次出现,这就是今天留给大家思考的问题:“文明”是什么?
从书中澳大利亚的原住民被限制在“保留地”不得离开、自生自灭的内容,我推荐了《黑麋鹿如是说》,这是北美印第安奥格拉拉苏族巫师黑麋鹿关于一生经历的口述史,在我看来就是一部印第安人的消亡史。这本书,我第一次读是在三十年前,第二次读是在十年前。
提问环节,今天换我提出问题:小土著托里内所知道的世界,与地理学家帕噶乃尔所认识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吗?为什么?
学者们都知道,两个人的世界是不同的。在书里,澳洲小土著托里内拿了地理课大奖,但他的老师,一位英国神甫教给他的地理知识是,世界都是英国的,亚洲是一个国家,首都是加尔各答;北美洲是在英国的约翰逊总督治下的美利坚合众国。这“异想天开的英国式地理学”,让地理学家帕噶乃尔哈哈大笑并放弃了试图去纠正托里内的想法。
“各位,两个人所说的,既是同一个世界,又是不同的世界。地理位置是没有争议的,但认知是不同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土著掌握的是老师传授的‘知识’,而地理学家帕噶乃尔是通过探索发现建立的对世界的认知。”我说:“现在的学习将不再以掌握知识为目的,知识是路径,要通过路径去建立认知。否则,就会像这两人一样,虽然同处一个世界,但对世界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帕噶乃尔为什么放弃纠正小土著?因为认知不同,两者不在一个维度,一个人认定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改变的,甚至接受不同的理解都很困难。”
“哦——毛豆,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教大人了。”一位学者恍然大悟说。
“你认为是为什么?”我问。
“因为大人的认知已经固化。”她说。
NICE!我对她这个观点竖起大拇指。虽然我也确实教不了大人。
甜点时间后,继续主题“孔孟仁义”。一个小时,就只讲了《论语》六则。两千年多年前没头没尾的只言片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学校里有标准答案,但我有我的解读。我们的目的不是去争对错,而是强调有不同。强调答案不止一个,甚至可能没有答案。”
在“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花了较多的时间。怎样“温故”?不是简单的像在学校里的刷题复习,那是对已知内容的重复;“温故”是“学而时习之”,学以致用,在实践中去运用。古音“能”和“而”同音,因此在我理解,这个“而”并不是表并列的连词,这前半句也不是“温习学过的知识,可以从中获得新的理解与体会”这个现在通行的解释,而是在学而时习之余,还能知新,面对未来和挑战去创造、创新,这样的人就可以为师了。这个“师”也不是现在老师的意思,更不是教师、警察、医生这样的职业。二千五百人为一师,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军队建制。师还指的是众人之首。什么样的人能成为首领?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集大成者和能力出众者就是“师”。也即是有学习能力,能进行知性冒险,带领众人去开创的人,就是师。就是梅贻琦所说的大鱼前导,小鱼尾随,师生从游的前导者,就是墨家的巨子。
“毛豆老师,那你觉得你是‘师’吗?”一位四年级的学者问我。
“叫毛豆,不要叫老师。”旁边七年级的“老”学者纠正说。
“从刚才我所解读的‘师’的意思来看”,我回答:“我还不配。”这也是我从讲谈第一季起就不称各位为学生,而大家互称学者的原因——我们都是学者——终身都在学并习之的人。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一则我指定一位五年级的学者来说说她的理解。过去两次讲谈,她都提出了自己对外星人是否存在的疑问。但我今早问她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有什么进展时,她说只是一直在想而已。“所以,这就是‘思而不学’了。希望今天回去后,对这个问题你开始去探索,去了解过去一百年来人类在这个领域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讲谈结束后,这位“外星人女孩”没有离开,而是又找到我,问:“毛豆,按说离太阳越近就越热”,她在白板上画了一座陡峭的山峰,山巅上站着一个小人,“那为什么登上越高的山温度却越低呢?”
“对啊,按说赤道是地球上最热的地方了,可为什么赤道还有雪山呢?”我也对她提出问题,“我知道,但我不想,也不能告诉你。你需要自己去寻找答案。下周讲谈,你把一周外星人探索的成果和这个问题的答案和大家分享,如何?”
“好的。我会开始去探索的。”她说。
对我来说,这就是讲谈的美妙时刻,尝试去启发行动和思考,而不是给出答案。任何学术都应该,而且要必然后胜于前才行。假如没有思考和探索,只能亦步亦趋跟在师后面,学什么“字字是真理”,那没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