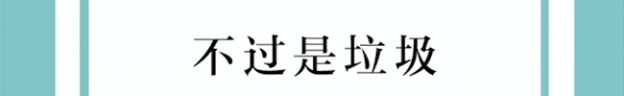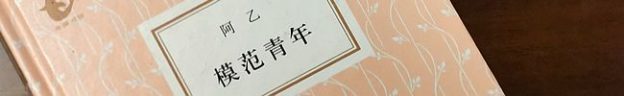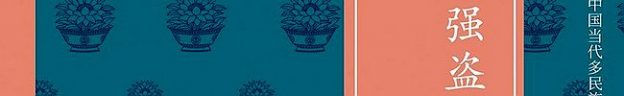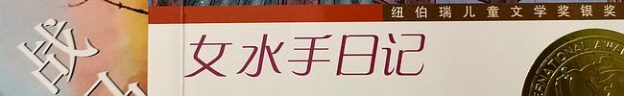阿托·帕西林纳《遇见野兔的那一年》,读过的第一本芬兰小说。已入围我“2025年度最佳图书”奖,值得二刷。
这是一个家住赫尔辛基的中年男子瓦塔南从不堪的生活和工作中逃离,回归自由的故事。遇见野兔只是一个偶然,或者说瓦塔南需要的是一个理由、一个借口,至于是一只野兔还是松鼠,不重要。
瓦塔南的工作有多不堪?“那是什么烂办公室,还有,什么烂工作!不就是一份成天揭发社会八卦的杂志,对真正该揭发的社会建设弊案从来只字不提。在每周的发行封面上,刊登的总是一张张成天游手好闲的家伙、选美小姐、名模、演艺世家新生儿的照片。瓦塔南曾经很满意这份在大报社里的记者工作,他曾一度很高兴能够有诸多机会去专访那一个个外界难以理解的家伙,甚至能采访到受政治迫害的人。他以前真的认为这是一份好工作,至少能为社会大众揭露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但随着年岁渐长,他甚至不再幻想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有用的事。他只顾着做好人家交代给他的事情,只满足于不添加任何评论的报道。他的同事们,一个个也都是失意且对未来不抱希望的人。”
他的生活也没好到哪里去。“瓦塔南并不爱太太,用一句话来形容,她很不贤淑。从他们结婚以来,她就一直令他难受,或者可以说,她很自私。她总是会买些很可怕的衣服,既丑陋又不太实用,而且没有什么场合适合穿,到头来连她自己也不再喜欢这些衣服。瓦塔南相信,如果换丈夫可以像换衣服那么轻而易举,太太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甩掉自己。”
在结束一次无关紧要的采访,回赫尔辛基的路上,瓦塔南与同事为在哪里投宿意见不合而吵了一架。他们一路情绪紧绷,麻木且疲惫。驾车的同事躲闪不及撞到了一只野兔,瓦塔南下车查看,发现兔子断了一条后腿,在为它包扎时同事驾车离去,他“终于办到了:独自一人在树林,穿着便装,就着夏夜,完完全全被遗弃在路边。”瓦塔南和野兔的自由之旅、心灵之旅就此开启。
在小村庄,瓦塔南遇到了友好的书报摊女孩和兽医,觉得“这个小村子实在很舒服,于是多留了几天。”;在森林里,瓦塔南遇到了森林大火和醉汉萨罗森撒利。那个夜间“景象十分虚幻:着了火的树木点亮了夜空,颤动的火焰看似开满在溪流两侧一朵朵的巨大红花。因为温度实在热得让人无法忍受,以至于在大火烧到溪边时,两名男子只能躲在溪流中央,也将大酒桶搬到溪流中,只露出头部,一面喝着酒,一面观赏这场由大自然担纲演出的毁灭奇迹。树林不断发出爆裂声,火焰在树枝上轰轰作响,一根根噼啪作响的细枝纷纷飞入溪中,这两名男子的脸在水面上显露着红光。他们一面笑着,一面开怀畅饮。”这种乐观、豁达的松弛感,在每天都是生命里的“关键时刻”,每天都生怕错过什么而急急奔命的城市人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然而,这才是生活。
在冬季到来前,瓦塔南搭上长途汽车,穿越广袤且人烟稀少的森林,“在沼泽边缘找了个栖身之所,是一座长满松树的小岛。他每周去西莫耶尔维两次,采买食物,并从公共图书馆里借几本书。这期间他读了很多好书。”这是我的理想生活,并且我已非常接近这样的生活——2024年就是我“遇见野兔的那一年”。这年搬到偏远小区,有家人和几千册书为伴,每周进城两三次,买书四五本,每天读读书,敲敲键盘记下点琐碎,不需要认识谁,也不需要在乎有没有人认识我。阿托·帕西林纳在书里说:“谁都可以过这种生活,但首先要能够知道弃绝另外一种人生。”
昨晚散步,和太座说,卸载手机里社交软件,只保留基本的通信,每天散散步、读读书,做点家务,保持思考,这样就好。
太座觉得我还是需要与这个社会保持一点必要的联系,因为有了输入,要保持输出才行。或许她是对的。但我认为自己记录一下就够了,更多的输出于我,不是非要不可的。
阿托·帕西林纳《遇见野兔的那一年》,中信出版社2017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42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