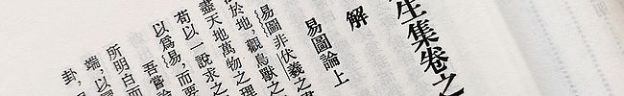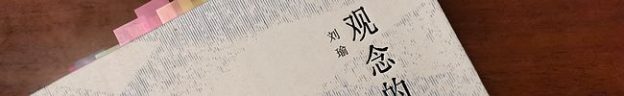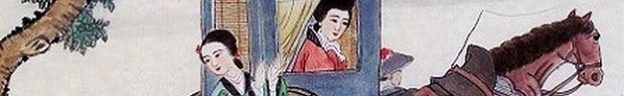最终,九年级女生H还是没来校上课,倒是在读《震川先生集》,并且在微信上与我保持交流。这封信,即是回复她读书之疑惑的。
————
H展信佳!
《震川先生集·卷一》的《经解》,确实如你所理解的,就是对经典的解读。如果对古文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没有较深入的学习,读起来就比较困难。所以对《震川先生集》的阅读,你选择了难度最高的一种打开方式,并且坚持读完,实在是……作为语文老师,我也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表达我的想法,只能说“太棒了”——不只是你的学习能力,还有学习的态度和耐力,都让我感到吃惊,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具有这种“韧力”的学习者了。保持这种坚韧,一旦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方向,很短时间就能超越大多数同行者,抵达学术人生的第一个高峰,那个时候我的建议就是留在那里,留在你的舒适区里,继续快乐攀登。
你上周说对《经解》读不太懂,网上也找不到资料,把能翻译出来的都翻译了,但还是不能理解,希望我能讲解一下。乐意之至。
《经解》第一篇就是论“易图”,我就先来尝试讲讲这一篇的第一段,如有不当或不同理解之处,可一起探讨。
易图非伏羲之书也,此邵子之学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以八卦尽天地之理,宇宙之间,洪织巨细,往来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于象矣。后之人,苟以一说求之,无所不通。故虽阴阳小数,纳甲飞伏、坎离填补、卜数只偶之类,人人尽自以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
中国私学的创始人是孔子,当时他教学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给数量庞大的学生们(弟子盖三千焉)上什么课、用什么教材。现成的,合适的就略作编辑或拿来即用,如《易》、《春秋》;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编,如《诗》。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被推到学术和思想的统治地位,于是这些孔子选用或自编的教材就成为了所有读书人的课本而被尊为经典,《易》就成为了《易经》,《诗》就成为了《诗经》,我想这就是归有光《经解》论《易》的原因。“易图”指的是河图、洛书、六十四卦方圆图等用于解读《易》的图形。相传《易》为“三皇”之一的伏羲所作,所以归有光说《易图》不是伏羲所写的书,而是邵子即北宋邵雍的学术研究成果。“子”是古时对有学问读书人(青青子衿)或学者的尊称。
庖羲氏的“羲”通“牺”,庖羲即庖牺,这里仍然讲的是伏羲。
“王天下”的“王”读第四声(音望),名词作动词用,解作统治意。
当年,伏羲统治天下之时,抬头仰望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低头观察世间万物盛衰的规律,以鸟兽身上的花纹与山川沟壑的地形为蓝本,创作了八卦,以此来通达神明的仁德和世间万物与天地的呼应。八卦表示的是事物自身变化的阴阳系统,用“一”代表阳,用“- -”代表阴,用这两种符号,按照大自然的阴阳变化平行组合,组成八种不同形式,因此叫做八卦。所以八卦涵盖了天地运行的法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来今为“宙”,宇宙在这里是一个包含我们生活和认知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这里面,不论是恢弘磅礴的还是细密微小的(“洪织巨细”解作《文选·班固》:铺观二代洪纤之度),过去现在天上地下的,生死及其之间休养生息的,统统都是我们分类和分析事物、认识世界的手段和方法,但后来的人们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奥妙。即便如此,后人仅只掌握其中的一种理解和解读方法,竟也能做到对世间变化解读的无所不通。因此,虽然日月更替阴阳变化的推算只是一种小小技能,纳甲卜卦原则和飞伏解卦方法、为水主陷险的坎卦和为火主兵戈的离卦之间的水火调和互补、五行推算之类的机巧和推算,人人都自以为能够掌握其中要点而都可以《易》来解读了。
以上即是我对《易图论上》第一段的解读。如果要将《经解》中全部文章照此解读,估计字数将在整个卷一字数的十倍以上,可以另成一书了。所以除非我们可以采用面对面的对谈方式,否则,建议还是从卷十五的“记”入手。因为如《震川先生集》点校者周本淳的前言中所说,归有光虽然在仕途上蹭蹬终生,但却博览群书且著作等身。在其研究成果中,又以散文最佳。他的散文“不惑于群言,不慑于势利”,以文笔朴素简洁、善于叙事而为人推重。我们如果选择从他的散文来打开《震川先生集》,来了解归有光和他所处的时代,应该会是更适合的切入口。
另,总是浸泡在《震川先生集》中,恐怕有时候也会疲劳,所以也可以看看闲书放松放松——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
窦德士《嘉靖帝的四季》
豆总 上
二〇二三年四月廿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