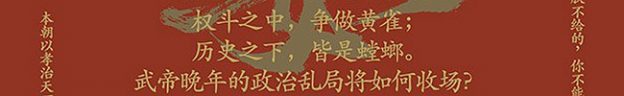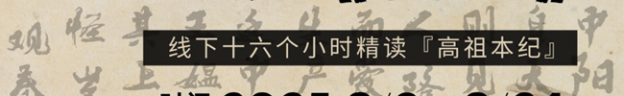“兴儒本只是刘彻和王太后向窦太后夺权的幌子,终其一生刘彻对儒学并无特殊的兴趣,但借着这次失败的变革,后世不断渲染汉武帝对儒学的推崇,最后发展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光甚至不惜模糊时间,把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定位在建元元年,将武帝接见董仲舒的情形含混地写成即位之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似乎他一登基就收到董仲舒的感召,可是董仲舒一生并未受到他的大用,只不过官至诸侯国的国相。”我在讲到这段历史时,选了《史记》和《汉书》相关章节来作比较,以证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这一段,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角度。初高中历史为什么“学不好”或“不好学”,最终以至于不得不靠死记硬背才能应付考试?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教科书里从来都是只告诉结论,不去做分析,更不接受讨论和不同观点。
“‘李广难封’是有原因的。李广长期为边郡太守,匈奴‘避之,数岁不入界’,这其实是说明他长于防守作战。司马迁描写过他与匈奴射雕者的遭遇战,这只能说明他个人骑射技艺出众。但率领骑兵大部队,在草原荒漠中远距离奔袭,指挥数万人快速机动、运动作战,则不能单靠主将武艺高超,而是另有一套办法。李广这次脱离城塞进攻匈奴本土,作为主将竟然被俘。在此后卫青围捕单于的漠北之战中,李广又迷路失期。另外一位宿将李息,景帝时已为将,武帝时的马邑之战中为材官将军,无功;以后两次出征匈奴,皆无功。这些事例都说明,以李广、李息为代表的,成长于文景之时的老一代汉军将领,在同匈奴作战时,他们的军事知识结构已不适应从阵地战、防守战转向进攻战、运动战的这一时代变动。”关于“李广难封”的新解读,我认为极有道理。
“元狩六年(前117年),大农令颜异因白鹿皮币一事被诛,罪名是‘腹诽’。此法一出,从此恶政无人敢谏。”这让我想到《1984》里的“思想罪”。
“虽然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最热爱记录历史的民族,但古代历史的记载仍然不足以让后人弄清楚许多事情的细节,许多真相也就因此湮灭……古代史研究比的是谁能在现有材料中看出新意,以及在材料缺失的空白处提出有创见的、逻辑自洽的和当下可见材料难以推翻的推理和猜想……已经发生的历史具有唯一性,但如果只能依靠破碎的残片去还原它,它就具有了丰富的可能性……我希望本书能激起读者对历史想象的热情,焕发读者推理历史可能的冲动。在符合以上限定条件下,读者自己做出的推理与猜想的价值不必任何学术权威差。”因为历史学能够被证明是实证的、客观的科学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谭木声《巫蛊乱长安: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83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