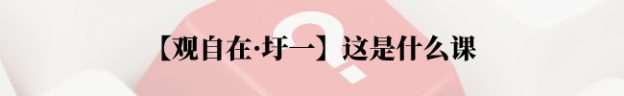昨天在学生群里发消息:各位同学,因本周主题内容有安史之乱和“唐七律第一”,是本学期课程的要点,所以本周语文课2、3都合班。另,请于31日11:45前提交各位的五月阅读简报。
今天的语文课,原计划要讲杜甫的《春望》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两首,但,确切来说,《春望》诗是讲完了,也只是算讲了关于这首诗三分之一的内容。
“嘛呀,那个黎明,这个星期咋个上得完这个主题嘛?!还好你及时刹车,否则怕是今天连这首诗这几个字你都讲不完哦。”下课一进办公室熊猫老师就开始表示担忧。
“不急,我们慢慢上。不卷、不等、不靠、不怨。我会把握好学期进度。”我说得好像一切尽在掌握似的。为什么今天教学推进如此?不是诸君不给力,全因诸君太给力。
“城春草木深”句,想引“庭院深深深几许”,忍了,怕收不回来。
“感时花溅泪”句,引了“花重锦官城”句对比,一悲,一喜。
“烽火连三月”,杜甫写下这首诗时正是安史之乱第二年,他北上灵武投效李亨时,于途中被叛军俘虏,与王维等人一起关押在长安。杜甫位卑无名,看管不严,在李光弼大军到来前成功脱逃,但王维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现在王维与杜甫对我们来说,一样是大唐天空中闪耀的星,但其实杜甫是到了宋朝时才为世人所重视。“嗯,我知道,宋朝时候文人的地位比武将要高。”就从某君这一句起,我就开始跑偏了——古籍以宋版为珍——书籍的印刷装订发展——赵匡胤为了不蹈之前五代均亡于武将之手的覆辙所以必须杯酒释兵权————北宋重文轻武几乎屡战屡败,但为什么经济文化却相当繁荣?这个我们下个学期讲到宋朝时再来细细讲吧。还好及时收手,结果诸君不依:“怎么还来个急刹车啊?一个下回分解的悬念一留就是留到下个学期?”
“好,我们回来说说杜甫位卑无名,到底他做了个什么官连叛军都懒得看管呢?”
我在黑板上刚写了个“左”字,“我知道,他做的官叫左—拾—遗?”白不太确定。
“不管确不确定,怎么想的就大声说出来。”
“就是左拾遗。”
“对啦!那这是个什么官?什么品级呢?”
有猜七品,有猜九品的,但竟然没人猜八品。
“杜甫这个左拾遗是个从八品的小官。在京城几乎连官都算不上。”
“那就相当于今天公务员的一个科长咯?”平时闷闷不吭声的杨问。
“嗯,差不多。拾遗是左省门下省言官,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以及尚书省下六部就是三省六部制。这种官制与科举制这种选官制度联系紧密。”于是中国古代三大选官制,略讲了察举制,刚到九品中正制就下课了。好吧,明天继续。
午饭后乒乓时间,中学部负责人黄老师带试读新生某来,说他听不懂语文课,想和我聊聊。我们坐在台阶上,“是听不懂、不喜欢还是不适应觉得有挑战?”我问。
“我不知道怎么说。”他怯怯说。
“不用考虑我的感受,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我们班的语文老师不这样上课,他讲诗就只是讲诗的意思,让我们背。你的课我不太适应。”
“班上学生从六年级到九年级,诗从一年级讲到高中。就像今天课上我讲的,中国的古诗词几十万首,会不会哪一首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你自己的诗,读出你自己的诗,慢慢积累从而构建你自己的人文架构,并通过独立思考拥有常识和判断。这是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学校和上课方式。这两种方式,你更喜欢哪一种?”
“我不知道怎么说。”
“不用考虑我的感受,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如果说满分10分,之前的课我觉得可以给5、6分,这里的课我觉得可以给7、8分。”
“如果只是不适应,可以慢慢来,慢慢融入。我们老师和学堂接纳和适应不断到来的,性格各异学习方式也各不同的学生;学生也需要适应我们各位老师上课的不同风格。有的人融入很快,而有的人需要多一点时间,这没有对错,不要担心,这是一个我们互相适应的过程。你是否愿意面对这个挑战,尝试去适应?”
“我会的。”他说。我们击了一下掌。
下午赵老师刀哥要带出国留学班的实验,我又代了一节生物课。“豆哥,这个课你能不能不要穿插地理、历史内容?”新生罗说。“做不到啊。生物多样性的原因就是地理环境的不同。”当第二节课铃声响起刀哥走进教室时,诸君掌声欢送我离开教室,他们想必也是受够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