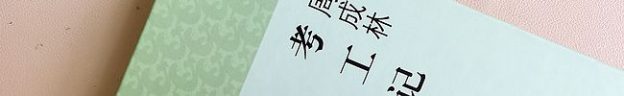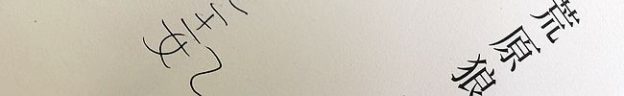一个人的家庭就是他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对将罗马作为人生奋斗目标的人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现实是,有的人他生下来就在罗马。有的人注定了一生挣扎,然而所有的挣扎都不过是不甘心、不认命,命运稍有改变与是否奋斗都没有关系,或许只是碰巧撞进了命运的裂缝里。歌里唱“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现实是“九分天注定,一分靠板命”(板命,即挣扎)。哪里有什么天道酬勤,这不过是为了安抚不断躁动的社会底层人的安慰剂,对只有靠不断奔波苦苦忍耐才能活下去的人画的饼,对现实不甘心试图改变点什么的人的麻醉剂,似乎只要勤劳就会有未来,未来就会变得更好——当你什么都没有时,至少你还拥有勤劳。然而这只是让你能有一口吃喝而已,然后继续期待永远也不会来的美好未来。如果天道真的酬勤,为什么最富足的不是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终日用尽全力才能活下去的社会底层?人世间的苦,难道只是因为他们不够勤劳吗?天地有何仁义?
周成林散文集《考工记》,加上序言共10篇对过去生活的记录,不做作,不高深,安安静静以克制的笔触,记叙了生活中难忘的点滴,写父亲、写母亲、写自己,顺畅而深刻。《考工记》是其中记录找工作的一篇。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一切都是被无形之手安排好的。你一出生就被注定了成分,不同的成分又注定了会有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家庭以及什么样的人生。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身份、没有生计,更罔谈生活——因为没有背景、成分不好的人就算得到了一份工作,也不过是社会最底层的、随时会被任何人取代的,收入微薄的活着而已。
周成林《考工记》,海豚出版社“海豚文存”书系之一种,2012年8月1版1印,三折淘来九成新二手书。总阅读量第1441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