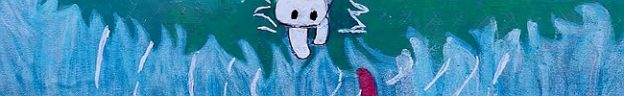“中学时期的老师、家长,总认为通过各种手段,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但中学教育的后果,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默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作为中学教育后续阶段的见证者,我目睹孩子们被牵引成长过程中的状态,对此有着深切感受,但家长对此并不知情,中学老师在应试目标的逼迫下,也无法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负更多责任。在疯狂的追逐中,没有人可以容忍孩子的失败,现实强化的高校分层,学生也不容许自己失败。孩子们的个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面目越来越相似,早已成为工厂的标准化构件。”
这一段,是我在2021年1月19日读完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后,从书中摘录的一段话,作为“读过”的“证据”留在了博客里。今天从书架抽出这本书,把四年半前在书里做的标记和笔记又看了一遍,算是二刷了。手上这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二〇年八月一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印,印数极少见的达到四万册,一本由一线教师撰写的关于中国教育的畅销的非“畅销书”。
之所以今天想起这本书,是早上把太座和两个娃送出门后,在家洗完碗、吸了尘、打了八段锦、晾了衣服,坐在阳台软椅上休息刷朋友圈时,看到贵阳市同在城市扶困融入中心的刘亚军,转发了一条《黄灯:我们的教育就像一场慢性的炎症》的演讲视频。视频里第一段话就是我读过这本书并留下的这段“证据”,以及“(黄灯)学生从来没有因为观点的不同,和我发生任何争论。也从来不会有过多的追问。讲台下的孩子,一届比一届安静。也许是多年应试教育的惯性,他们经过无数次紧张的课堂,数不清的题海战术,千百次的考试……这种过度的透支,早已磨损了他们的青春锐气”,于是让我突然想起读过的这本书,于是忍不住也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视频,并加了一段文字——
每次在也闲书局上午的讲谈结束后,我都会问在书局大厅自习的女儿:“你在外面,会不会觉得我们在里面很吵啊?”女儿通常说还好,那我就真的觉得还好了。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还好”,就是有点吵但又不至于让外面的人难以忍受。如果讲谈只是“我说你听”,没有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争论,那实在是一场灾难,不如回家自己一个人看书的好。
上周六,上午的讲谈结束,请各位学者把上上次的作业给我时,新来的书尧妹把手放在书包里,亮亮的眼睛看着我,怯生生问:“作业本上可以画画吗?”
“当然!那是你的本子,你当然可以随意装饰它。并且,如果你觉得画画更能表达你的想法,为什么不呢?”
听我这么说,她才把手从书包里抽出来。手里拿着的本子,原本简单乏味没有装饰的牛皮纸封面整个成了一幅画:一个布满绿草,开满鲜花的花园里,一只白猫在池塘边,试图抓住水里正在游动的红色的鱼,猫的爪子拍打水面泛起的涟漪一环一环扩散开来,直到“教师:哈基豆”这几个字。整个画面构图严谨,色彩丰富而柔和,不但有动有静,而且极有层次感。我现坐在书房敲这些字,瞟了一眼手边的这个本子,为了保护这封面,书尧妹还用透明包书纸将本子的封面和封底包了起来,但我恨不得把这个封面撕下来,用画框装起来挂到墙上才好。
我猜,如果我说不可以在本子上乱写乱画,她就不会把本子给我,而不交作业的理由大概率就是“不会写”或“忘了”,那我们都会错过这一幅美妙的画,这一份真实的表达和一份发自内心的友善和接纳。同时,不论本子里写了什么,有多少字,都一定是她当下能够做到的最好。而我也在“巨豆”、“魔豆”之后再次喜提“哈基豆”这个更加萌的新学名——也闲谈学者给我的新名字。
一个孩子身上的东西,投射出来的肯定是他背后的家庭。书尧妹家住在城外的村里。在哥哥参加了两季的也闲谈后,四年级的她加入了这三季。每周六,父母轮换着送兄妹俩进城到也闲书局参加讲谈,往返几十公里。我总在想,两个小时的讲谈,平均到每位学者的时间不过十分钟,山长水远而来,真的值得吗?我又为他们提供了什么呢?
上周,一位老友问到我在也闲书局的讲谈的情况,我说参加讲谈的学者们,有来自重点中小学和私立学校的,也有来自城里公立学校和村里面的学校的,有在学校上学的,也有无法进入当下教育体制下的学校的,这个小小的讲谈就是中国当下教育的缩影。
关于“教育”这个话题,我身边人人都关注,都在谈论,可什么才是“教育”呢?从约翰•杜威到萨尔曼•可汗,从柏拉图到赫胥黎和保罗•弗莱德,从朱光潜到郑也夫再到黄灯和林小英、顾远……关于教育的书读过三五十本,在教学一线工作过近十年,可我还是说不清楚什么是教育。
敲到这里,想起上周六,结束一天的讲谈后,一位刚升入九年级,从第一季就加入的学者和我一起去地铁站。路上我问,对他来说讲谈意味着什么,他说除了在学校和家里不可能有的思考和平等对话、表达的机会外,还“认知到学校教育的局限性和无知”。或许,这也是“教育”之一种罢。
一个小时,拉拉杂杂敲了两千多字,快十一点了,肚子开始有点饿了。要出门去买一把葱(或者从某位邻居的菜地里薅一把),中午吃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