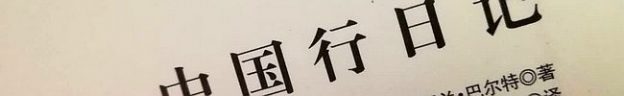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战局会议。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指定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国立长沙联合大学。1938年2月中旬,临时大学又迁徙昆明,4月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12月21日,西南联大第九十八次常委会议决:“自本学年起,本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定为一年,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按年轮值。本学年本会主席应请由梅贻琦先生担任。”后因张伯苓、蒋梦麟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在昆明,故实际没能实施轮值制度,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一直由梅贻琦担任,主持校务工作,直到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结束为止。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中华书局2018年5月1版,2021年6月3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的《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收录了梅贻琦从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日记要言不烦,只记天气、大事、人事和应酬,家事基本只限于孩子,偶有所感,也是点到为止,并不铺陈。但因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所以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样,是了解、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日记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作为日常闲书来读,就大可不必苦大仇深,反而会从琐碎里面读出一些“人味”和有趣来。如:
“早九点后起,殊感不适,渐觉作冷。至午前十一点余,冷益甚,乃上床盖被三四重,尚不觉暖,而冷至发抖。至一点余,冷渐止,而烧作矣。三四点时,徐大夫来诊视,烧至三十九度余,嘱食Quinine,每次两粒。(繆云台夫妇约作旧年除夕宴聚,郁文携彬、彤同去。关雨东饭约亦谢。)”都病成这样了,还能记录下来几点烧到多少度,这不是自律,是“肌肉记忆”罢?!
“上午在联大办公处,至十一点出,赴梨烟村,郁文于五六日前感冒卧床,尚未痊愈,但热度已不过三十七度以内。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随手随处,皆是好景致。
“昨晚甚闷热,但上床即睡去。清早醒来发现帐中有二蚊,俱是满腹热血,惜贪食过多,飞转笨重,竟因口服而捐生矣。”两校的校长,经常跑警报不说,每天应酬频繁、校务繁重,竟在日记里“惦记”两只蚊子,足见真实。
昨晚睡前,给幸福学堂Y校长发了一条微信:“我今夜枕边书《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民国时人物,很多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尤其在非常时期的日常记录,虽然琐碎,但更显真实。现在也是“非常时期”,在公众号开一个“幸福日记”之类的“纪实”栏目,哪怕每天絮絮叨叨零零碎碎,会不会反而成为一个宣传和招生的“亮点”?毕竟,现在能好好说话不喊口号,有笔力又保持阅读和思考的校长,寥如晨星。”发者随心,回者随意。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总阅读量第1349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