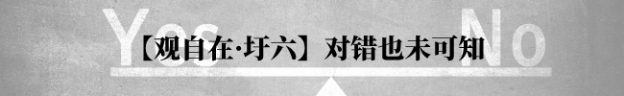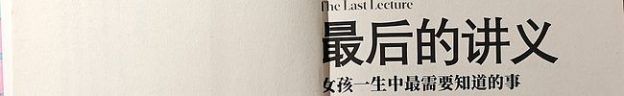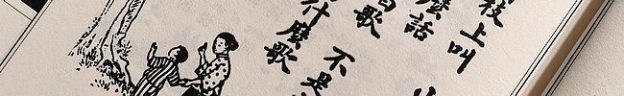“如果有一个能够与人交流的机器人,我们要让它做什么呢?”我想,如果机器人真的能够实现与人交流,那就说明这个物体已经具备了自主意识,成为了生物意义上的“物种”,而不是现在的ChatGPT这样基于在预训练阶段所见的模式和统计规律,来生成回答,还能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真正像人类一样来聊天交流,甚至能完成撰写论文、邮件、脚本、文案、翻译、代码等任务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了。那时就不能再用“它”,而是应该用“祂”了。
“人的能力是有高低之分的。技术越发达,越需要能力的支撑,因此人类的能力也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提高……技术并不是以固定的速度发展变化的,而是呈指数级变化,因此,在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无论哪个时代都会有幸福与不幸,这就好像‘零和游戏’一样。因此,我们不能仅依靠未来会怎样、幸福不幸福这种单纯的价值判断去评价。现阶段,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定义绝对的幸福,全都是相对的价值观。”所以在人生中“最好不要做那种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比如,因为辛苦就放弃或者觉得这样做很轻松,这样的选择往往会让自己后面更辛苦。如果找到了真正想去做的事,或者觉得这件事能够让自己拼命去做,那么放手去做就好了。”
“肉体对于人类的定义来说并非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即便没有肉体,我们也能够成为100%的人类。”那人类的定义是什么?这本书出版于2022年,石黑浩当时说:“即便是身体完全不能动的人士,只要有了‘脑机接口技术’,就可以完全操控人形机器人。”还不到两年,2024年3月,马斯克就实现了人类第一例脑机接口。
“如果‘个体’被统合,或许进化就会停止。所谓进化,就是在繁育出的诸多个体中留下优秀个体。”但我认为,不论是“进化”还是“退化”都应当是演化,留下更适合当下环境的个体以实现种群的繁衍。
如果这是你人生中的最后一天,你会讲述什么?日本NHK电视台大受好评的纪录片《最后的讲义》完全版四种之一,石黑浩《最后的讲义:一千年之后的人类与机器人》,海峡书局2022年6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43本。我在书名页写:“一个大男孩和他机器人玩具的故事。”
翻过了一千多本书,少见的遇到了装订错误,有16页的重复内容,也算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