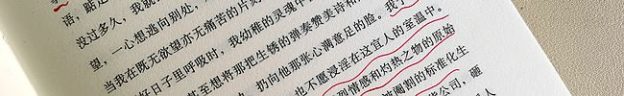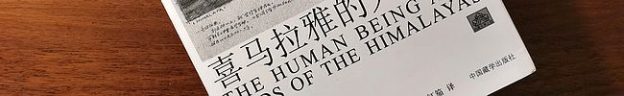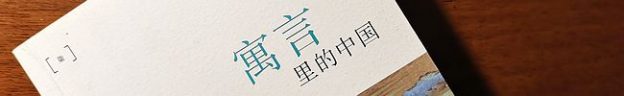当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没有得到足够的滋养支撑不了这具肉身的存在时,那感觉就像一天没有进食引起的汗出如浆、四肢瘫软、两耳轰鸣、思维停顿的低血糖反应。这时在口里含了一块巧克力,想吃快点使症状迅速得到缓解,但又舍不得让它融化太快使得这片刻的美好太快消逝。这块巧克力就是黑塞的《荒原狼》,想一口气读完又舍不得读完。这种阅读的巧克力感在读《悉达多》时也没有过。
继续读《荒原狼》,《哈里·哈勒的笔记》中的独白简直就是我的日常白描,以至于终于、突然明白,我这26年的职业生涯的前19年“尝试过的事情、换过的工作不计其数”(太座语),而竟然在幸福学堂今年已是第八年,并任教过从四年级到高中的语文、历史、地理、阅读写作、摄影、游学、基础经济学、中文经典、社会实践等学科以及自媒体编辑和图书管理员等同样“不计其数”工种的自我深层次原因:
“白日逝去了,如往日那般逝去了。我消耗了它,以我粗疏羞怯的生活艺术,温柔地耗尽了它。我工作了几小时,翻阅了几本旧书,忍受了两小时上了年岁的人才有的疼痛;我吃了药,并为药物蒙蔽了疼痛而感到高兴;我练习了呼吸,又偷懒省去思维练习;我散步一小时,发现了绘于空中的几簇羽毛状云朵,它们美妙精致、珍贵难得,我惬意得如同读旧书。但是——总体而言——这一天既不令人心醉,亦不光彩照人。它并非幸福喜悦的一天,而是长久以来,我早已习惯的庸常一天:一个不满意的老男人的不温不火、不好不坏,适度愉快又尚可忍受的一天。没有特别的痛、特别的忧,没有实际的苦,也没有绝望。这样的一天,我既不激动,亦无恐慌,而是中肯平静地思考着:是否到了像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一样,用剃刀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
“谁若品尝过另一种不幸日子的滋味:痛风发作,抑或那些灵魂死去的日子,那些内心空虚绝望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我们身处被毁坏的、被榨干的土地上,人类社会和所谓文明,朝你龇牙咧嘴,步步为营,毫不松懈地将你那患病的“我”,逼向难以负荷的绝境——谁若品尝过这种地狱般的日子,谁就会对今天这庸常又不好不坏的一天感到格外满意。他会感激地坐在温暖的壁炉边,感激地阅读晨报并确信:今天既没有爆发战争,也没有建立新的独裁政权,政界商界没有曝光肮脏的丑闻。他会感激地为那把生锈的古琴校音,随后弹奏一曲适度欢快又带有近乎消遣意味的赞美诗。这首赞美诗让那位温柔安静、被溴液麻醉的似是而非的满意之神倍感无聊。在这种温吞的气氛中,在这种令人满意的无聊中,这两位——频频点头又似是而非的神,花白头发、吟诵赞美诗的似是而非的人,同样心怀感激又无痛无苦。他们相像得如同一对孪生兄弟。
“心神满意,无痛无苦,度过可以忍受的平庸一日是件好事。疼痛和欲望在这种日子都不敢大声喊叫。一切都轻言细语,踮足而行。只可惜,对于这种满足,我恰恰无法忍受。没过多久,我就会在难以为继中仇恨它,憎恶它。我满怀绝望,一心想逃往别处,尽可能逃向欲望,必要时逃向痛苦。当我在既无欲望亦无痛苦的片刻,在寡淡无味又不温不火的所谓好日子里呼吸时,我幼稚的灵魂中便生腾出剧烈的悲苦和愁闷,我甚至想将那生锈的弹奏赞美诗和感恩曲的琴,仍向昏睡的满意之神,扔向他那张心满意足的脸。我宁愿忍受恶魔般的痛焚烧我的心,也不愿意浸淫在这宜人的室温中。不消一会儿,我心中就会燃起对强烈情感和灼热之物的原始欲望,燃起对这种了无生气、平庸乏味、被阉割的标准化生活的怒火。我疯狂地想去毁坏、去粉碎,因为我所诅咒的、最为厌恶的,首先是这种市民气的满足、健康和惬意,这种精心维护的乐观,这种被滋养驯化的中庸和庸常。
……
“在我们过的这种心满意足的日子里,在市民气十足又精神匮乏的时代中,在眼下这些建筑、这些店铺里,在政治家和人群中,要捕获神的踪迹多么困难!我怎能不做一匹荒原狼,一个可怜的遁世者。世人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世人的欢乐不是我的欢乐。我无法理解,人们在拥挤的列车和旅馆,在嘈杂又充斥粗鲁音乐的咖啡馆,在优雅的奢华城市酒吧和戏院,究竟能找到什么乐子——成千上万人追逐的快活,或许我也可以去追逐,但我无法分享。与之相反,我经历的为数不多的快乐,那些愉悦、狂喜、巅峰体验,世人或许最多在文艺作品中见识过、寻觅过、热爱过。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必定认为那不合常理、荒诞不经。确实,如果世人是对的,如果大众娱乐是对的,那我就是错的,我就是疯子。我就如我时常自诩的一样,是匹真正的荒原狼,一头迷失在它无法理解又深感陌生的世界中的野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