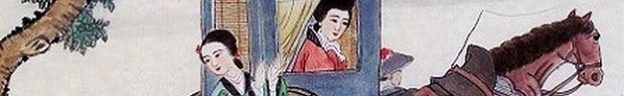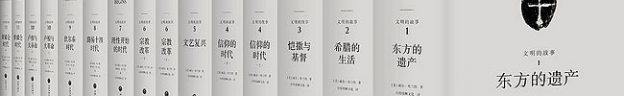这是一片盛产皇帝的土地。土地越是贫瘠,当皇帝的冲动就越是不可阻遏。他们眼中闪动着亢奋和凶险的光焰,自告奋勇地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不幸的是皇帝的名额只有一个,四海之内,只能有一个真龙天子。为争夺这个法定名额,他们彼此间要打出狗血,把流血和死亡当做自己的选票。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吴三桂不服朝廷撤藩,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开启“三藩之乱”,反了。19岁的康熙在昭仁殿里迎来了他执政生涯的最大危机。
说起大清王朝的开国功臣,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吴三桂。那不仅仅是因为在1644年,统领关外兵马的吴三桂背弃了与李自成已经达成的默契,把潮水般的大清军队放进关内,导致大明王朝彻底倾覆和李自成的功败垂成,更因为他紧紧咬住败退的李自成紧追猛打,直至将他彻底剿灭;在这之后,又替大清王朝铲除了南明政权,用弓弦残忍地绞杀南明政权最后一位皇帝——永历皇帝,让大清王朝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保持皇位的稳定是最大的道德,在此之上不再有什么别的道德。于是,“宁杀三千,不放一个”就成为中国皇帝最执着的信条。康熙无疑也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与吴三桂完全是半斤八两。
康熙与吴三桂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爆发,根本原因是,在极权社会,存在着一种权力守衡定律,即:权力总量是一定的,一个人的权力增大,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权力减小。即使在皇帝与臣子之间,这一守衡定律仍然存在。因此,康熙与吴三桂之间为争夺有限的权力资源而爆发的冲突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个性的冲突,而是命运的冲突。他们或许都不想冲突,但他们都躲不开。
有清一代,中国的皇权专制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值。这种皇帝权力的最大化固然带来了清初的盛世,但是“一统就死”的效应并未发生改变,空前的盛世,是以空间的禁锢和僵化为代价的。
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昭仁殿: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2016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8本。“故宫秘境文丛”六种,全部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