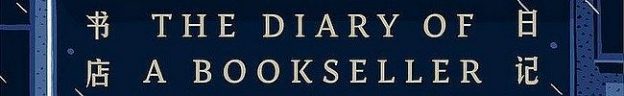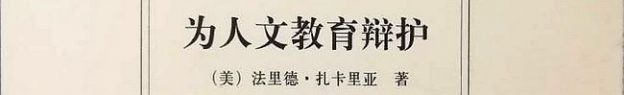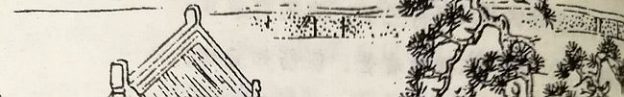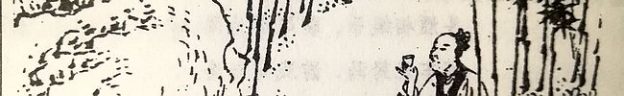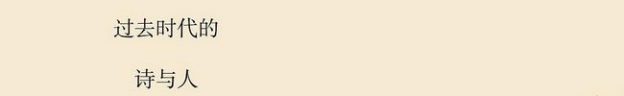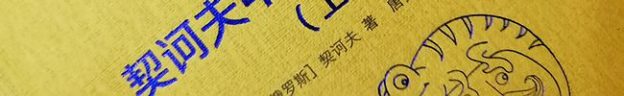每个月固定要加三箱油才能维持。一箱400元左右,三箱在1200元上下。两箱汽油饮车,半箱饮我——每个月买书的钱大概也是半箱油钱。
受疫情影响,年前买的书,今天还没发出来。还好家里有“存货”,否则就要等米来下锅。手边三本“古诗十九首”的书,都是这几年东一本西一本不知道怎么就闲散来的,还派上了正经用场。看完“古诗十九首”,就要到唐诗,书架上王力的《诗词格律概要》和《诗词格律十讲》,不晓得能不能读懂,之前随便翻了翻,困难。金圣叹选批的唐诗六百首和杜诗,还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必须要读的;还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伦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有必要读。读不完!怎么办?
最好先读点其他的缓解一下紧张和焦虑。
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人文教育辩护》,新星出版社2015年11月1版,2018年6月2印。我把读库出品的这种10万字以内,小巧轻便一册,半天就可以翻两遍的“通勤口袋书”叫做“读库本”。前段时间还看过另一本“读库本”——莉迪亚·派恩《书架》。读库出品的“读库本”,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兼顾,而且比“企鹅小黑书”还要更“冷”,我会留意旧书市场。话说,淘到的三辑“企鹅小黑书”通勤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货。
之前看过一本书,好像是《大书特书》,乔·昆南说有的出版商和作者反感旧书市场,因为旧书的买卖让出版商和作者无利可图,甚至利益受到损害——这笔钱本来会用去买新书。现在我很难去分析清楚到底是先有读者再有的作者和出版商,还是反之,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但我知道的是,旧书交易让更多的人读到了更多的书,也让更多的书被更多的人读到,这好事一件。当然,在这一点上,电子书也做得很好。
现在读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抵制电子书常被视为守旧、不合时宜。不过还是有两点让人欣慰:也是在前段时间看的一本书里写的,虽然看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但总体的比例并不大,没有超过20%,纸质书仍然大有市场;老的死掉了,年轻的加入了,看书的人数大概还是维持在一个数字上下,但因为人口总量变大了,所以显得好像这个群体的人数变少了。以前一条巷子里住了10家人,怎么样都会碰面点个头打个招呼,见面次数多了偶尔也会聊一聊。现在还是那一条巷子,但层层叠叠住了200家人,就谁也不认识谁了。
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人文教育辩护》,大概五万字,我翻了两遍,并且以后可能还会再读,并推荐给其他人(除非有人要求,否则我通常不会这么干)。这本小书读完,大体留下如下几句脚印:
1、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们,包括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就是追寻真理。
2、耶鲁大学于1828年发表了一篇报告,为经典科目辩护。报告指出,人文教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教授任何特定职业所需,而是为所有职业的共同点奠基”。
3、查尔斯·艾略特认为人文教育应该允许你选择自己的道路,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由此实现独特的自我。但很多人认为(学校里)有些科目不值得教授。艾略特的办法是,让教师提供学生所需,而学生则选取他们所爱。
4、要想了解一个问题,可以看书,或是直接用网络搜索。真正难以做到的,是学会用批判的眼光来阅读、分析、陈述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享受知性冒险,把思考作为家常便饭。
5、大部分事实,都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没有必要占用脑资源来记忆。最好的思考往往在不同的理念、领域和专业发生碰撞时出现。
这两周在拟新学期图书馆增补书单。现在疫情依旧紧张,百业凋敝,要不要把“企鹅经典小黑书”列入学堂新学期图书增补申请单里?什么时候能开学还是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