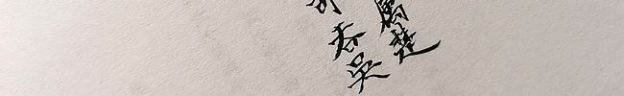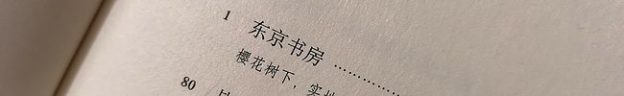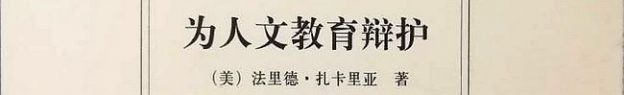“钱穆十岁在无锡一个叫做荡口镇的小镇上新式小学——果育学校,教唱歌的老师华倩朔曾留学日本,是全校师生共仰的中心,不仅擅书法,也能画画,而且能诗词,音乐更是他的专长,自编的教科书由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风行全国一二十年,里面的歌词都是他自己写的,尤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他在小学高年级时,国文老师精通历史地理,经常有精辟之论,他说自己中年后喜欢史地,即源于这位老师的影响。还有一个终生不忘的老师,是小学时,暑期讲习班教过他古文,他说自己做学问喜欢从历史演变着眼,寻究渊源宗旨所在,就是从这个班上得来。他在这里读了四年小学,七十年后追已,他感慨在离县城四十里外一个小镇上的小学,竟能网罗这么多的良师,既有深厚的旧学基础,又能接受融会新学。以后的岁月要在乡村再求这样一个学校,恐渺茫不可复得。那时,科举初废,老师在镇上受到普遍尊敬。他举了一个例子,华倩朔曾在苏州一个学校兼课,每周往返,每当他乘船穿镇而过,当地人沿岸注视如同神仙自天而降。这样的故事此后哪里去找?”
“小学关乎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小学提供的是文明的底线教育,它绝不是今天升学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一个环节,而是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不仅是知识的启蒙,更是人格的熏陶与训练,是全方位的人的教育,是精神成人的起点,和大学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许多人所受的学校教育可能就是小学,不一定有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但他在一所健全的小学所获得的滋养,足以在精神上支撑他的一生。”
昨夜本打算看电影,最后还是翻了书。在《读库1105》,也就是11年前的2011年11月的一期《读库》里,读到傅国涌《过去的小学》一篇,以上两段即摘录于该文,越读越是感慨当下教育的不堪,更惭愧自己忝列教职,在追随前辈的路上也给学堂校歌填词,也在语文基础上努力兼顾历史地理,但还是难望前辈项背。截至目前,对我而言最好的睡前读物还是《读库》。一晚上一个“有趣、有料、有种”的中篇,一本正好可以打发一两个星期。
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只晓得看书的速度比不上买书的速度,所以床上书每个星期都在增加,只是不晓得到底有好多。今天晴换床单被套,搬上搬下就清楚了,截止今天的数量是不多不少80本。争取年底时读得只有40本。
新学期花卷上六年级,我就是她在学堂和在家的语文教师了。新购小楷毛笔数支,想试试语文作业能不能从这个学期开始用毛笔批改。上个学期跟曙光老师学了两天小楷,虽然是杈杈字,但传递的是一种语文该有的样子和学无止境的态度。
晚上,花卷和闺蜜的语文课,讲的是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