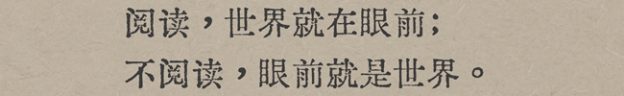上周讲谈作业之一的“末日图书馆”,要求每位学者必须将一本对自己最重要的书放入末日图书馆,以确保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并用二百以内文字介绍所选的书和原因。
第一环节,就请各位学者分享自己选的书。有选日记的,因为想让关于个人的记录得以留下来,让后人看看前人是如何生活的;有选军事百科全书、实验百科全书、航天科学史和《人类简史》、《白夜行》、《德米安》的,可以让后代了解到人类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有选《天工开物》和《辞海》的,前者可以帮助末日幸存者,在没有现代科技的情况下进行基本的生存工具、生活器具的制造;后者可以确保后人能够通过这本工具书,读懂前人留下来的这些书。
“这些书都很‘有用’,但我觉得有一个遗憾”,我说:“竟然没有人想要放一本诗集在这个图书馆。我想问问是什么原因让各位没有选诗集。”
“很多诗都读不懂啊!”我一听到这个原因,就觉得坏了,那一刹那甚至觉得学校的语文课,讲到诗歌时应该要请一位诗人来讲才对。我认为,诗不应该有什么目的,诗本身就是目的。
“诗不是拿来‘读懂’的,各位,诗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诗不是用来理解的。诗是对话,是和自己的对话,和生活环境的对话。当你每天在吃饭、劳作,劳作、吃饭这样最基础的生存之外,诗是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之必要。今天是中元节,当你夜深人静独坐窗前,看到皓月朗朗,脱口而出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是‘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首诗,你读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才是你的诗。”我继续问:“你们认为人与牲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思想。人有思想,而牲口不会有。”
“太棒了!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思想,就是行尸走肉,不是‘人’。而诗,就是思想刹那间的火花和表达,是赋予一具行尸走肉以灵魂的刹那。”不是人人都是诗人、都能成为诗人,但生活一定要有一点诗意来抵抗日复一日的乏味和疲惫,否则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那毛豆,还有机会的。你不是还没有选书放进图书馆么?”
然也。可是那一刻,我竟不知该放谁的诗集好了,是《诗经》、《王右丞集》、《河岳英灵集》、《寒山子诗集》,还是《草叶集》、《先知》、《爱是地狱冥犬》?我困在了自己的莫比乌斯环中,却没有想起我最喜欢的诗人和诗集——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和他的《一只狼在放哨》。
在介绍了中元节后,从这个主题中伯罗奔尼撒战争交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进入“苏格拉底的广场”讨论环节:什么是正义?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诸君各自发表自己对‘正义’的理解,以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从此开始思考。一番讨论下来发现,所谓的“正义”,常常随着立场的不同而不同,正义与非正义从事件的发生到结果一串互为影响因素的推动下,似乎只能从某一个事件或片段来界定,而一旦进入连续的时间流中,两者之间的边界就变得模糊起来。由此我展示了新古典主义画派奠基人雅克·路易·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并讲了这幅画所描述的故事。道德与法律、战争与和平、国家与个体、公正与特赦、亲情与仇恨全部熔成一炉,而这往往就是真实的生活,怎么办?可能我们一生都在思考,也是一生都有可能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没有说的是,可能这就是生活的意义之一种。
再从雅克·路易·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到《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口的拿破仑》,路易十六、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皇帝。上午的学者们想知道后续,我说关于后续我们后续再说;而下午从这里就进入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关于为什么要阅读,我在PPT上敲下忘了从哪里得来的一句话:阅读,世界就在眼前;不阅读,眼前就是世界。
可惜,我对上午从三年级到七年级所对应的年龄、年级带来的阅读理解能力的差异的准备还不够,有的学者的阅读进度已远远超过讲谈要求,而有的还没有跟上来,因此我只进行了原计划内容的十分之一。“各位,不管读不读得懂,读就对了。”课本里的内容不够丰富又过于碎片,而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就是集合了各种写作手法和创意的表达范本。下周起,将用一个小时,也就是讲谈的一半时间来就文本中的精彩部分进行讲解,并和大家讨论,提出更多的“为什么”,慢慢去了解和认识,什么样的是真正“好”的东西。
下午的学者对《战争与和平》这样的“细糠”接触太少,并且九年级的课业压力很大,于是我们用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要就一个问题展开讨论:在前七十页里主角是谁。学者们觉得是安德烈、皮埃尔、瓦西里公爵,但又觉得似乎都不是,似乎并没有主角。然而我认为,其实主角是安娜·米哈伊·诺夫娜·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她的出现总是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每次出现都带着很强的目的性。她出现在女官安娜·帕夫洛芙娜·舍列尔的晚宴上,在周边欢快的氛围中独自哭丧着脸,但在见到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库拉金公爵时“一刹那,她露出了微笑”并“一旦拿定一个主意,不达到目的,绝不肯罢休,如不能如愿以偿,就准备每时每刻纠缠不休,甚至大吵大闹。”而随着她从想让独生子鲍里斯进入近卫军开始,一个接一个的主意,或者说是欲望一个接着一个,推动她去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为达目的甚至介入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别祖霍夫伯爵的遗产继承纠纷中,并最终击败瓦西里公爵,帮助皮埃尔,伯爵的私生子成为新的别祖霍夫伯爵。这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将各个人物和事件串起来,并让事情尽可能向着她希望的方向(也是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去发展。虽然她的身上没有通常畅销小说中的主角光环。
“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经典,真的是要‘啃’的。一旦‘啃’下来,”我指着外面也闲书局那满坑满谷的几万册图书说:“很多书对你们来说,就真的是‘一览众山小’了。”一旦完整读过这样精美绝伦、纤毫毕现而又恢弘磅礴、雄浑孤傲的作品,市面上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不必再读,因为拿起来翻一翻你就会发现里面的注“水”量有多少,是否值得自己为之花时间。
今天的作业,除了阅读,还有——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二卷中,借苏格拉底、格劳孔、塞拉西马柯、西摩尼得等人之口,对“正义”进行了辨析。西摩尼得认为正义就是“把对每个人有益的东西恰如其分地给他”,这个定义引申出来就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善恶终有报。塞拉西马柯认为“正义无非就是强者的利益。”格劳孔认为“守法践约叫作合法的、正义的。”在这里,正义意味着遵守法律,践行社会契约,不去伤害他人。柏拉图还提出正义就是各尽其职的观点。而中国人将英国法谚“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译为“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你认为什么是正义?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
一天的讲谈结束,离开也闲书局时,在旧书区淘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1版1印影印版《听雨闲谈(外二种)》,内收桐西漫士《听雨闲谈》、程穆衡《燕城日记》和许锷《后湖櫂歌百首》。四十多年过去了,依旧纸清墨明,一笔一字,一注一印,读来皆极度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