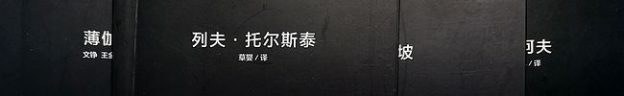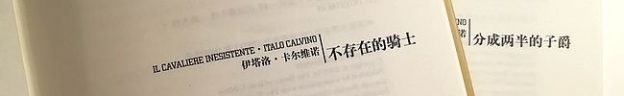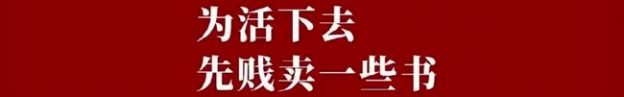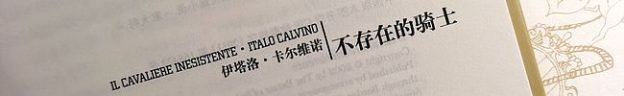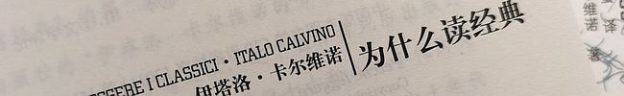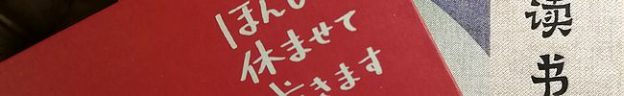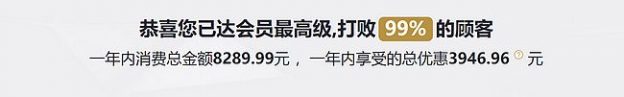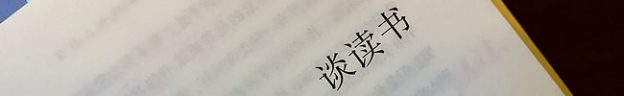女儿的咳嗽好些了,儿子支气管肺炎在医院住了八天,今天也出院了。不用一天往返六趟医院,我就可以有点时间读书。
在读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前,要重刷一遍《企鹅经典:小黑书》第一辑,因为下个星期中学部语文课的课外阅读就要从这套书开始。今天刷了前四本,薄伽丘、爱伦·坡、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一个比一个精彩。边读边想要怎么和中学生(其实只是六年级)讨论和解读这些经典。
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可笑。我一个上世纪高中毕业来临时代课靠阅读自救的打酱油老师有什么资格解读经典?怎么解读都是误读。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它有很多种“误读”的可能提供给读者,读者能从其中“误读”出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甚至全部。这就是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说的:“只有那些你在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只有在非强制的阅读中,你才会碰到将成为‘你的’书的书。”但是非常不幸,这些书多少也算是强制阅读,因为虽然是课外阅读内容,但也是在课程计划之内。
之所以在语文课外要求课外必读书,是因为“当代世界也许是平庸和愚蠢的,但它永远是一个脉络,我们必须置身其中才能够顾后或瞻前。”而“经典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所到达的位置。”对于经典“出于职责和敬意阅读经典作品是没有用的,我们只应仅仅因为喜爱而阅读他们。”而要做到“因为喜爱而阅读他们”,就需要一个发现的可能,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他不知道的,要知道更多,就要先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就需要学习人类对物质世界以及精神世界探索的结果总和——“知识”,从而才可能诞生出“智慧”进而可能领悟到“一切诸智慧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胜者”的“般若”。
前天?昨天?还是大前天?记不太清楚。大概应该就是在这个“五·一”假期。有天晚上,女儿做错了什么事,忘了,只还记得我很生气,对她说,知识可以治愈无知,但拯救不了愚蠢。
能拯救愚蠢的只有智慧,知识只是智慧的基础,而且还是不完全的基础,所以我认为知识与智慧没有直接的关联,知识可能会升华出智慧,但也并不是常常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