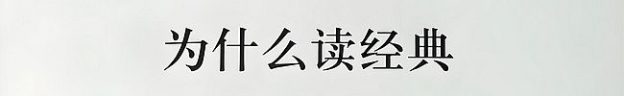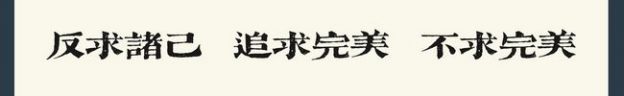“豆总明天要去露营吗?”昨天有学生问我。
“不去。”我说。
“为什么?”
“我不会撒谎和找借口,实话实说就是不想去,所以就不去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解释曾经在户外行走就是我的工作,而我不想再去重复这样的事。这就像十四岁时曾被某一本书感动过,但四十岁再读毫无感觉,不是那本书或阅读这件事不好,而是作为主体的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不同了。
“嗯,明白,这是你的原则。”
今明两天是开学欢乐周的露营活动,有包括我在内的部分教职和行政人员没参加。校长认为全校的活动原则上所有老师和同学都应该要参加,学堂的教育理念鼓励学生要有勇敢、敢于尝试的品格。所以,作为老师也应该身体力行,真正的接纳这样的教育理念,成为愿意接受挑战的人。这次露营活动没有参加的老师,除根据《员工守则》要求的特殊原因请假外,其他都将计入事假。
原本我对不参加活动还有一点忐忑和愧疚,这一被事假,就释然了——坦然接受自己的选择带来的自然后果。
最近在读周濂的《正义的可能》和罗翔的《法治的细节》。
穆勒的自由原则要求人类事务尽可能少受限制,认为这会激发人最大的创造力,总体上促进社会福利。但斯蒂芬却看到反面,他非常冷静地看到人类中相当比例的人群自私自利、感情用事、好逸恶劳,经常陷入琐碎的日常事务不能自拔,给他们天大的自由,也不能让他们有分毫的改进。
两个角度、两个极端,似乎都有道理。但凡事有多种可能性,让一个人在尽可能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哪怕是像我这样经常陷入琐碎的日常事务不能自拔者也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这不就是自由吗?以欢乐周为例,不(不能、不愿)参加某项活动或所有活动者,在不强制的前提下鼓励其提出自己的欢乐周方案,并助(要求、鼓励、帮助、督促)其去实施、实现,这不也很欢乐吗?!
斯蒂芬有著名的关于强制的三原则。他认为强制在以下情况中是不合适的:
(1)强制的目的是有害的;
(2)目的正确,但强制手段不适合达到目的;
(3)目的正确,手段也能达到目的,但付出的代价太大。
很显然,全体参加露营活动从初衷上不属于第一原则。但即便是后两个原则,任何程度的强制参加集体活动的手段都是不合适的。
学堂推崇自由、平等、尊重等品格,并强调要真实生活,真实表达,鼓励老师要活成真实的自己,这样学生也才有可能成为真实的自己。这样的教育理念非常棒。但什么是尊重?什么是勇敢和愿意接受挑战?什么是真实?对权威敢于说不,这算不算勇敢和接受挑战?算不算“身体力行,真正的接纳这样的教育理念,成为愿意接受挑战的人”?对这些词语和概念的理解,需要反思,需要换位思考,更需要同理心和同情心,以及接受对同一件事不同看法的理解和包容。
以露营这件事来看,校长希望所有师生都能参加,并将是否参加视为是否接纳某种教育理念的行为标准,在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体系里,再正常不过。然而我们换一个生活中的日常事例角度来看,这样的价值判断并不一定就正确。绝大多数人旅行可能会选择高铁,而选择步行或自行车骑行的人,是否就意味着不认同高铁的存在、不认同高铁出行的人的选择?很显然不是,因为这与价值判断无关,只是不同而已。并且如果经过长期学习和训练,每个人都能从日常生活中无意识的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和独特的,要尊重每一个人,那就不会轻易掉入不参加集体活动就是不接受某种价值或理念的二极管思维和评价中。
人非生而知之者,生活即是学习,因为知易行难。学校有多接纳老师的不同,老师就能多接纳学生的不同,这样也才能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路漫漫其修远兮,轻以约,故人乐为善,每个人都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