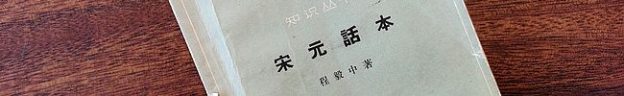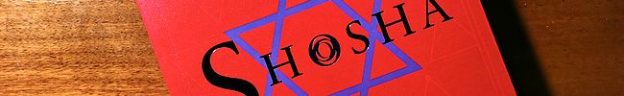语文合班,开讲新一个主题。
在抛出“李贺”这个名字前,先讲有一位诗人只活了27岁,和王勃一样英年早逝,重温“初唐四杰”。
再讲杜甫这个中二视大唐为自家的,心系天下,我们如果知道他的身世就不会对他这种想法觉得奇怪。杜甫的外婆是义阳王李琮的女儿、李世民的孙媳妇,所以杜甫也是个拐着弯的皇亲国戚。杜甫有个表弟叫李晋肃。李晋肃的先祖叫李亮,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叔父,是李世民的叔爷。杜甫有个侄子,也就是李晋肃的儿子,因为老爸的名字里“晋”与“进”谐音,而被禁止参加进士科考。这到哪里说理去?!这李晋肃的名字也不是他自己起的,关他儿子什么事呢?然而,那时候就是这样的。
第三讲王维,人长得英俊潇洒,诗写得好,又懂音乐,画也画得好,还出身于唐朝“五姓七望”一流家族里的太原王氏,被称“诗佛”。元稹虽然出身贫寒,但一样风流倜傥,诗文俱佳,最终官居宰相。李晋肃的儿子,杜甫的侄子,诗也写得好,还和刘禹锡写“竹枝词”一样开创了个人的诗歌风格“长吉体”,但因为莫名其妙的那个原因不能参加科考,诗写得“鬼诈”人又长得不好看“鬼孚孚”的,于是后人就称其为“诗鬼”。他就是——李贺。
“那‘长吉体’的诗是个什么样的?”被称为“黄金水稻兄弟”的“地理天才”邹问。
“好好好,这个问题问得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长吉体’的诗是个什么样的。先从这首《马诗》开始。”
从“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讲唐诗的“比”,以物比物,就是比喻;“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讲“兴”,就是借物抒怀,借物咏志。讲了一个学期的唐诗到这时,“比兴”就是一点就通了。
“快走踏清秋”的“走”,讲了古时的走非现在的走,而是跬—步—趋—走—跑,即是现在的跑,而“跑”则是现在的狂奔。
一节课讲了一首诗,李贺《马诗二十三首·其四》。
午饭后,“历史天才”沈带了一张他手绘的冷兵器时代两军对阵图找我,问我这仗怎么打。我看了,说从地形和兵力来看,如果调配得当,应该是看起来兵少的一方胜。他说是的,但不知道怎么就胜了。我说:“你换位作为两军统帅,看看这仗怎么打,想好了来找我,我再说说我的想法。”一会儿,他新画了一张更详细的,标注了兵种、战场和地形的对阵图来。我问:“作为弱的一方统帅,你分析看看自己有哪些优势。”他一二三四五,“很好,我再给你补充两点……这样弱的一方采取守势,利用太阳的方位,还有村庄和树林的地形,就能给予敌军以毁灭性打击。我不知道历史上真实的这一战是怎样打的,但如果我是统帅,这应该就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战斗部署。”我说。
沈说:“是的,历史上这一战确实如此。你猜一下双方伤亡人数比。”
“防守方伤亡500人,进攻方伤亡两万?”我猜。
“差不多。这是英法百年战争的第一场战役,英王爱德华三世就是这样几乎全歼法王腓力六世大军的。”
“还真是这样啊?!”我有点惊喜了,“这是那一场战役?”
“克雷西战役。”
“所以看到没?地理和历史的重要性!”
今天是语文期末笔试《AI时代的教育》和中国历史期末笔试《我的2024》的提交日。
六水大人的《我的2024》,“改变最大的,当然是我自己。以前上课,我可是话都不敢说。怕讲错答案,不敢举手,还得要在老师面前保持好学生形象,什么都听他们的,只有这样,他们有好东西时,才会想起你。每天都要伪装自己,真不知道我是上学还是当间谍。到这可就不一样了,每天本就很轻松,情绪不会过于紧张。也不知道是什么影响,我变得不会与人交流困难,应该是情绪放松的原因。这个2024对我来说,真是奇妙的一年啊。”
“历史天才”沈说:“2024算是我活到现在最传奇的一年了……我比以前更明确了我的目标与未来”,说到何为历史,他写:“我认为历史不光是过去所被记载的人物、朝代、国家、战役,历史还包括过去和未来。过去已成为历史,而未来也在成为历史。历史不仅仅是这些,还是每个事物,每一个瞬间。”
诸君的《我的2024》,也就是我2024这个学期代课语文和中国历史的期末成绩单了。现在是我到幸福学堂的第八个年头。这几年里,每个学期我上什么课或者上不上课,都在反复调整,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在变,我能做的也就是做一天和尚就好好撞好这一天的钟,万事努力,万事随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