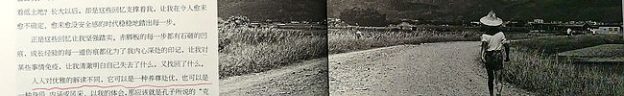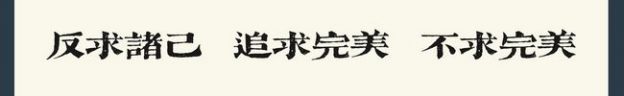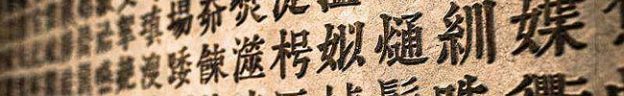德川幕府近江彦根藩主,同时也是当时知名茶人的井伊直弼(1815—1860)在其所著的《茶汤一会集》前言中说:“茶事之会,为一期一会,即使同主同客可反复多次举行茶事,也不能再现此时此刻之事。每次茶事之会,实为我一生一度之会。由此,主人要千方百计,尽深情实意,不能有半点疏忽。客人也须以此世不再相逢之情赴会,热心领受主人的每一个细小匠心,以诚相交。此便是:一期一会。”
在幸福学堂,每一日的课程于我,亦力求“尽深情实意”,盼同在学堂求学诸君能“领受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
在每个六周的评估简报里,会比较详细谈及参与课程的每位学习者的学习态度、作业情况、学业成就等方面内容;而期末惯例,我会为选一个字,作为他/她这个学期在我所任教中文学科的学习状态、所取得成就和不足之处的总结。东汉时许劭、许靖兄弟有月旦评,我称这个期末的一字评语为“一期一字”。
这“一期一字”,亦与日本在每年的年末,用一个汉字来概括一年世相的“今年の漢字”活动相似。这个活动由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从1995年开始主办,为的是让日本国民加深对汉字的关注和理解,加深对文化的认知。我的用意也在于此。一字一词、一诗一文、一时一世,如何看待和理解,这背后的文化往往注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走向和一个人一生的际遇。
这个学期我上三门课,六至九年级中文(自编教材人文综合)、中国历史和出国留学中心的中国文化常识,评语中用到的有莳、迟、菶、璠、丨、屮、芊、萏等字——
莳:《说文》:更别种。《方言》:莳,立也;莳,更也。[宋]杨万里《插秧歌》: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唐]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迟:《说文》徐行也。《广韵》久也,缓也。《注》缓而不迫也。《诗·采薇》行道迟迟,载渴载饥。[宋]刘永《少年游·长安古道马迟迟》: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唐]杜甫《江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唐]王维《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
菶:《博雅》:菶菶,茂也。《疏》:梧桐之貌也。《诗·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璠:《说文》璵璠,鲁之宝玉。孔子曰:美哉,璵璠。远而望之,奂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二则孚胜。《注》璵璠,美玉。《阮德如答嵆康诗》良玉须切磋,璵璠就其形。[汉]曹植《赠徐干诗》: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唐]李白《赠别从甥高五》:鱼目高泰山,不如一玙璠。
丨:《说文》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读若囟,引而下行读若。囟,《说文》头会脑盖也。,退也。意即已找到和掌握学习的方法,能做到联系古今上下贯通。若孜孜不倦努力向上,则能抵达极高之境界;若不奋力向上,则如蔤藏入泥。
屮:《说文·屮部》屮,草木初生也。《徐铉曰》屮,上下通也。象艸木萌芽,通彻地上也。
芊:《说文》芊芊,草盛貌。《博雅》茂也。[唐]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唐]韦庄《长安清明》蚤是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五代]李珣《渔歌子·楚山青》:草芊芊,花簇簇,渔艇棹歌相续。《文选·宋玉<高唐赋>》仰视山巅,肃何芊芊。李周干注:“芊芊,山色也。”
这个学期给花卷的评语是“萏”字。荷花含苞未放为菡萏,已盛开为芙蓉。[魏]曹丕《秋胡行》:芙蓉含芳,菡萏垂荣。[唐]李商隐《赠荷花》: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清]龚翔麟《菩萨蛮·题画》:田田初出水,菡萏念娇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