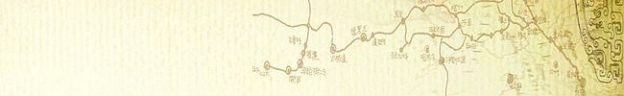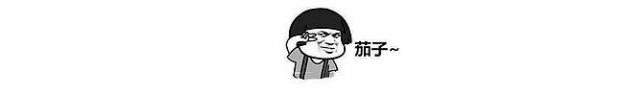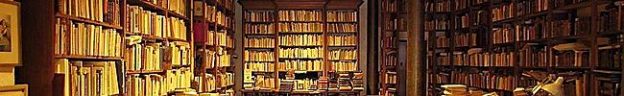“地理老师现在不骂我了,但是历史和语文老师把我骂得好惨。”昨天下午,小莽子一边对我说一边从书包里抽出几张卷子,“这个星期我的历史和语文月考都不理想,这几个题做错了。”
我接过试卷,历史还好,主要问题集中在商鞅变法;语文选择题错了一道,阅读理解丢了十几分,四十分作文得了三十一分。
“你知道为什么商鞅一变法,秦的国力就大大增强了?”
“不知道,老师没讲,书上只是写了‘商鞅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秦国的国力大为增强’这一句。”他拿起我书桌上七年级上中国历史课本,翻到35页,指着课本说。
“秦人比其他六国人更聪明吗?”
“不。”
“更强壮吗?”
“也不。”
“秦国的兵器与六国的大不相同吗?”
“应该都差不多的,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时代,而且应该秦的生产力还要比其他国家更落后点。”
“那商鞅的变法涉及了哪些领域‘使秦的国力大为增强,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一跃成为最强的诸侯国’呢?”
“涉及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
“这几方面的变法都改变了什么?为什么一变国力就增强、军队就强大了?商鞅为什么功劳这么大但死得那么惨?商鞅能不能不死?”
“呃……不知道。”
“好吧。那我们就从商鞅为什么不论变法成功与否都不得不死说起吧。”
用了半个小时,算是解决他的历史课问题。
语文选择题,要求选出一句没有语病的句子。小莽子选的B,老师的标准答案是C:我只有以大学为目标,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才能报答父老乡亲的大恩大德。
我长长叹了一口气。
“叔叔,我语文是不是差得有点老火?”小莽子有点紧张,眯起200度又不戴眼镜的小眼睛看着我说。
“不是,我觉得这一题,你选A、B、D哪一个都不算错,只有C这个标准答案才是错得最离谱的。”我知道不应该在学生面前说他老师的不是,但我一定要告诉小莽子,这次真的是他老师错了。
听我这样说,小莽子的眼镜眯得更厉害了,可能是想看清楚我的表情是不是认真的。
“我来告诉你这个选项C错在哪里。首先,读书是你的权利,如果为了报恩德而读书,这个是‘道德绑架’;第二,上大学绝对不是读书的目标,它只是读书的过程而已,就像幼儿园毕业上小学、小学毕业上中学一样自然;第三,如果要报答别人,首先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上不上大学,只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评判,更不是结果,你怎么评判一个足球运动员和一个铅球运动员谁更优秀?”
小莽子只是看着我,没有任何的回应。
“好吧,我们继续来看看你的阅读理解和写作。”
“‘《论语》十二章’学完了,老师让写学习心得,我不知道怎么写。”
“十二章都懂吗?”
“懂。老师都讲过。”
“那第一条‘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什么意思?”
“学习了之后,经常温习巩固,不也是很快乐吗?”
“老师是这样讲的?”
“是的。”
“可是,你不觉得这有问题吗?学会了不断温习巩固,这有什么好快乐的?你天天都看同一本书,快乐吗?”
“呃……看起来简单,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习’在这里不作‘温习’解,应该是‘实践’,引申为‘常常在实践中应用’,即‘学以致用’的意思。”
“可是课本上是写的‘温习’。”
我翻到七年级上语文课本第五十页,“时习”的注释真的是“按时温习”。
“《孟子》里面讲‘尽信书,不如无书’,教材不一定就完全正确,老师也不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你的心得知道怎么写了吧?其实关于阅读和写作,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能给你的建议就是:多读,多写。阅读不要受教材限制,越广越好;写作不要被套路框死,要好好说话,说人话;最后,要思考,要问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每天有半小时的阅读时间,但学校没什么书,都是教材上这些,我都读过了。我能不能借你的书去学校看?”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呢?你想看哪方面的?”
“下个星期历史课要上到‘张骞通西域’了,我想先多了解一点。”
“好说。”
“啊?你们在说西汉啊?卫青、霍去病打匈奴吗?”花卷咬着一根泡筒走进来问。
“对啊,哥哥下周历史课要学到我们吃的胡萝卜、石榴和葡萄最先是从哪里传来的。”我一边回答花卷一边爬上书架,抽出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 : 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还有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从书之一刘德增的《秦汉衣食住行》和许晖的《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香料在丝绸的路上浮香》,五本书放在桌上,“自己选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我说。
小莽子选了刘德增的《秦汉衣食住行》,“叔叔,我下个星期来还你,我现在要去上面亭子写作业了。”
送小莽子回来,太座大人说:“你不应该那样讲他老师,小娃娃很单纯,这可能会让他对老师有看法,影响他的学习,而你又不是他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