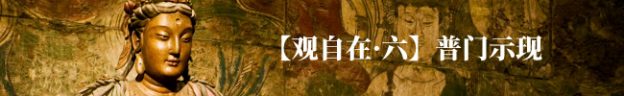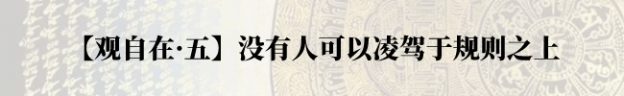昨天,这个学期新转班来的学生张,把“每日一记”语文作业设计成了一个问卷式的,开放式结尾的故事,在故事后问是否需要重新提交一份“正常小记”,以及“我会在语文方面继续写出优秀的作品”。
我留言:“正常小记”的“正常”定义是什么?是你认为的“正常”?我认为的“正常”?还是数学老师认为的“正常”?我觉得这种方式的写作,很有创意。我相信你能写出更加优秀的作品,期待!
学生沈在啃大部头的欧洲史,问可以不可把“每日一记”写成读书笔记,“为什么不呢?”我说:“你想,那就去做,做你想做的,没有比这个更棒的。”
下午到家,收到B君的邮件,想着晚上回信。但困极,把二娃盘上床后,九点半不到,花卷还在洗漱我就睡着了。
今天午饭后,曙光老师来,送我一卷他手书的赵孟頫《梅花诗》,“这是我当下能够达到的最高程度,没有落款是因为我会达到更高的高度。”我低头、弯腰,双手接过来,“这幅字装裱后会悬挂在我新的书房里,我的书房也将因这幅字而变得书香馥郁。”我说。
下午上完课,洗了手,戴上耳机,打开邮箱,仔细读B君的来信——
豆总:
见字如面。
我此刻在悉尼城中的一个犄角旮旯给您写信。
学生到悉尼城中已有月余,越发觉得孤独,寂寞。时常回想起在学堂做过的荒唐事情,或惹人发笑或觉得羞愧难当,但总归还是怀念还是难过,难过这时光匆匆从眼前中呼啸而过而学生却从不觉得。难过才短短数年学生已没有了少年心气,没有了“一诺千金重”的少年心气。
托您的福,学生虽然偶有拖延却再也没有了舞弊的坏习惯。这样最多害害自己,也不会丢学堂的脸面。
今日早起看到您给X君写的信,醍醐灌顶而一扫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阴霾。仿佛今日的悉尼城也没有往日那么讨厌,仿佛朝阳也要耀眼些。又惊叹于豆总的神通广大相隔千里数月未见也能为学生指点迷津。学生沉思许久,为此次求学之旅起名:“问心”,意喻对自己诚实,无愧于心。但不论学生最后做什么决定,以什么为生,富贵也好,落魄也罢,总不会忘记在学堂的点点滴滴。
我用近一节课的时间来平复心情后开始敲回信——
B君,见信如晤。
昨天下午收到你的来信,很开心,但忙于家务,未及细看,打算晚上细读后回信,谁知晚上困极倦极,只得早早睡下,所以迟复为歉。
今天上完课后,我洗了手(手上满是粉笔灰,大概我是学堂唯一、也是最后一个还在用粉笔板书的,从这你也能看出我的“老派”和落伍了),戴上耳机,将音乐从Fluke的《Absurd》换为藥師寺寬邦的《般若心经》后,仔细读你的来信。读到你称这次求学之旅为“问心”,“对自己诚实,无愧于心”处时,起身去接了一杯水喝——如果这时我独自在书房而不是在办公室,定会涕泪横流,放声大哭。不是悲伤,不是难过,是心生欢喜,生大欢喜!“能观心者,究竟解脱;不能观者,永处缠缚。”(《大乘心地观经》)与自己诚实相处的人能诚实地觉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能柔和对待自己。这种“柔”不是弱,而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我相信,悟性极高的你现正与自己柔和相处,也这样与他人相处,与世界相处,这是你已抵达,而我正在努力修行的方向。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正是学堂这段缘分让你我“心心相印”(《六祖坛经》),忍不住道一句“善哉”。
学堂的那段时光,我觉得应该会在你的人生里产生超出你预期的绵长影响,因此你或许会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仍然怀念,而“羞愧”则大可不必。因为有许许多多人都像你和我一样,曾经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有过彷徨的时期。幸而有几个将自己彷徨的经过记录下来了,例如我们的这番通信,例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个极妙的轮回安排,而且这不是教育。这是历史。这是诗。”
而孤独,是永远无法逃避的。只有面对、接纳孤独,才能享受孤独所带来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因为孤独是精神层面,而不是肉身的独自一人。但多数人无法忍受这种孤独,于是需要在群体中寻找和获得安全感。但事实是,他们愈是无法面对自己独自一人,就愈是孤独。谁能忍受,甚至是享受孤独,诚实面对自己,坦然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接受,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你的问题,谁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接受自己,和自己诚实相处就能走得更远,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孤独的旅客,因为一路上只有我们自己与自己相伴。
今天,鸟山明去世了。他的《龙珠》伴随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熊猫老师说:“我感觉我的那个时代正在消失。宫崎骏去世,我一定会大哭。”我说:“要开心,不要哭。每个人都会离开的。”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过客,我们能对自己做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人生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接受,接受分离,接受世事无常,接受挫折与孤独,接受突如其来的变故和无力感,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去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无法改变的。
我现在每次一进入中学部大厅,都仿佛还看到你站在大厅中央,正大声朗读《滕王阁序》。而那时和现在的我所做的,就是霍尔顿一直想做的事:一大群小孩在一大块麦田里玩游戏,旁边没有人——我是说没有岁数大一点儿的——我是说只有我。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把他们从那儿抓过来。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回头看你在学堂的那段时光,你会发现,你现在想要挣脱的,就是未来会怀念的。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至于往后的人生到底会怎样,往前走吧,总有一天会到达那个远方的。
另:听X君说你在读季羡林的作品,甚慰。
另:读信,看来还是应身处静室,燃香一炷,净手正坐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