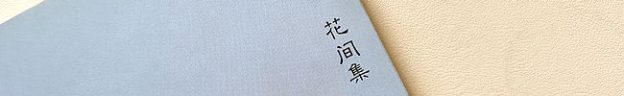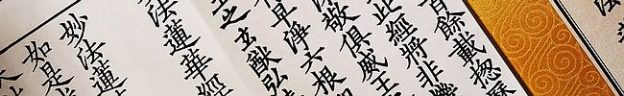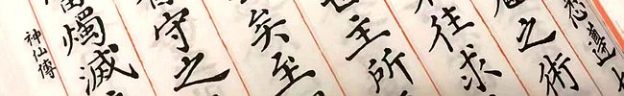课余翻完中国最早的文人词总集——五代后蜀赵崇祚编选晚唐至五代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十八家共五百首词集《花间集》。总阅读量第1342本。因其中普遍风格偏于浓艳华丽绮罗香泽,给花卷的暑假课程只选得十首。计温庭筠一、韦庄一、牛峤二、张泌二、毛文锡一、顾夐一、孙光宪一、李珣一,列于下:
蕃女怨
唐·温庭筠
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玉连环,金镞箭,年年征战。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
上行杯
唐·韦庄
芳草灞陵春岸,柳烟深,满楼弦管,一曲离声肠寸断。
今日送君千万,红镂玉盘金镂盏。须劝,珍重意,莫辞满。
梦江南
唐·牛峤
含泥燕,飞到画堂前。占得杏梁安稳处,体轻唯有主人怜。堪羡好因缘。
江城子
唐·牛峤
鵁鶄飞起郡城东。碧江空,半滩风。越王宫殿,蘋叶藕花中。帘卷水楼鱼浪起,千片雪,雨蒙蒙。
南歌子
唐·张泌
柳色遮楼暗,桐花落砌香。画堂开处远风凉。高卷水晶帘额、衬斜阳。
河渎神
唐·张泌
古树噪寒鸦,满庭枫叶芦花。昼灯当午隔轻纱,画阁珠帘影斜。
门外往来祈赛客,翩翩帆落天涯。回首隔江烟火,渡头三两人家。
甘州遍
五代·毛文锡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
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蕃奚。凤皇诏下,步步蹑丹梯。
荷叶杯
五代·顾夐
记得那时相见,胆战,鬓乱四肢柔。泥人无语不抬头,羞摩羞,羞摩羞。
定西番
五代·孙光宪
鸡禄山前游骑,边草白,朔天明,马蹄轻。
鹊面弓离短韔,弯来月欲成。一只鸣髇云外,晓鸿惊。
渔歌子
五代·李珣
荻花秋,潇湘夜,橘洲佳景如屏画。碧烟中,明月下,小艇垂纶初罢。
水为乡,篷作舍,鱼羹稻饭常餐也。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1版1印《花间集》,错误多,注释几近于无且不准确,插图是莫名其妙的乡村油画,文字忽简忽繁,版本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