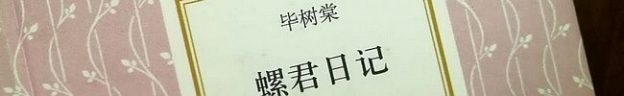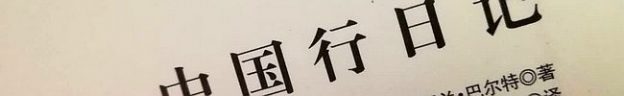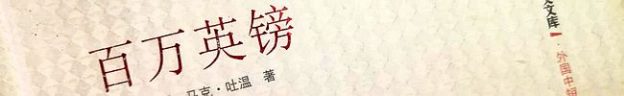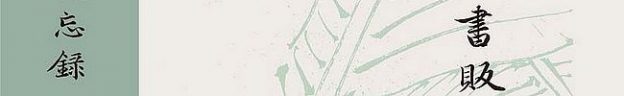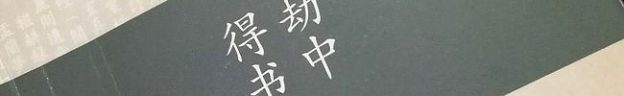禅是什么?大珠慧海说“饥来吃饭困来眠”,六祖惠能说“循指见月”,赵州从谂说“吃茶去!”《五灯会元》读了五年,读完估计还要再五年。
2014年买《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以为也是一本能够让我停不下来读个十几遍的,1996年3月18日在安顺市新华书店买的德国人欧根·赫里格尔《学箭悟禅录》(现译名《弓与禅》)由习弓而习禅的修行之路那样,充满了禅趣的,学习摩托车修理而悟出禅机的,油污而不油腻的机修工修行手册。或者是切·格瓦拉《摩托日记》那样,生命因旅行而改变的。啃了大概一个月,现实和想象之间的距离还是几个光年,现在还只剩得一句:我们常常太忙而没有时间好好聊聊,结果日复一日地过着无聊的生活,单调乏味的日子让人几年后想起来不禁怀疑,究竟自己是怎么过的,而时间已悄悄溜走了。这本书和禅有没有关系,我说不好,但肯定和摩托车维修没有关系。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不是一本历史书。是一部获得2005年波灵格大众伍德豪斯喜剧奖的小说。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买的新书。我笑点太高?都已经看到五十二页了,八十四岁的尼古拉都要和三十六岁的瓦伦蒂娜结婚了,我还没有找到值得一笑或笑得出来的点——如果这场婚礼就是的话。通常,一本书,要是我给了它十页的机会都没能虏获我,它就会被放逐,插回架上好几年、十几年或终其一生都吃灰。所以,我已经忍这本书够久了。
一天的翻书时间用掉了一半,换一本没看过的“新”书开得了头收不了尾,影响睡眠。就再看一遍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上一次看起码是在十年前,香格里拉至今未到,计划过一次,结果病在了半路,转道大理和腾冲。还记得在腾冲,客栈老板闲聊问我是不是老师,我说是之后,他一副“一切早已被我看穿”的表情,然后疑惑地指着我的耳环和手上的佛珠,问:“学校允许你这样?”我说:“我是先成为自己,然后才是老师。”
手上这本《消失的地平线》吴夏汀、朱宏杰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也是旧书,定价20元,4.8元淘来。后素环衬角上有一枚蓝色“文轩连锁眉山书城售书章”,三苏家那里。167页,12万字,刚好。
“乐府”有双璧:《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中国文学有双璧:《诗经》和《楚辞》;史学有双璧:《史记》和《资治通鉴》;清代戏曲有双璧:《桃花扇》和《长生殿》。我的书架上也有双璧,不是毛边签名本,不是佛经《古兰经》《圣经》,也不是古籍。一是美国人罗伯特·M.波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是英国人玛琳娜·柳薇卡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只靠书名就可以在豆瓣三星半打底。
阅读是旅行,有时很好,有时很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