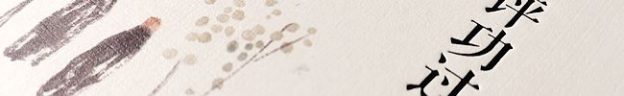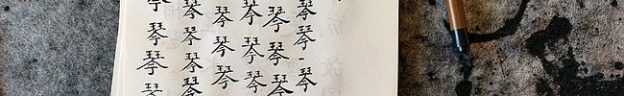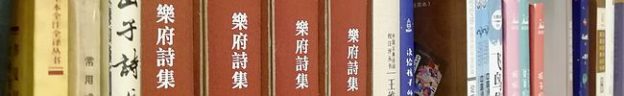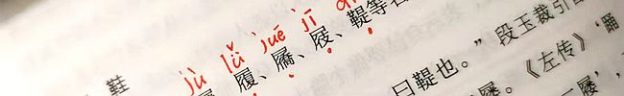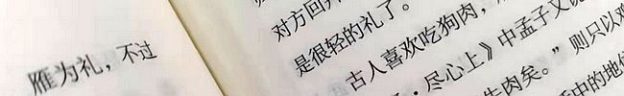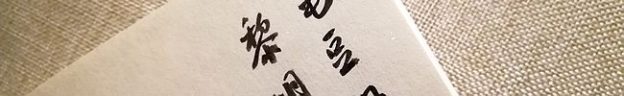来新夏“古今人物谭丛书”之《评功过》,二〇二二年读完的第一本书。普及读本水平,浅显易懂,适合中小学生课外阅读。
从一本书延展阅读出去,而家里又没有那本书,要想忍住不买,好难。昨晚陪女儿宵夜撸串,说起寒假阅读安排,她说希望家里再多一些适合她读的书。马上摸出手机,和她一起在“多抓鱼”选了十六本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旧书,包邮一百〇九元,平均每本七元不到。
学堂为鼓励学生阅读,明天(周一)上午安排了图书馆课程,让家长直接把孩子送到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并让孩子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和一百元钱,办理借书证。和女儿商量后决定明早她和我去学堂,不去图书馆。
首要原因是去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时间成本太高。和女儿算了一笔账:从家开车每周往返一次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里程超过四十公里,耗时一个小时,每次能借书三本。停车费、油耗和路上的时间成本,我们完全可以每周买三本书。如果有阅读扩展的需要,偶尔可以就近去开车五分钟就能抵达的区图书馆或进城去也闲书局。
然后,女儿年阅读量超过一百本,已渐渐形成自己的阅读脉络。家里的书有近三千本,其中近一千本是为女儿准备或她自己挑选的青少年读物,这已是一座家庭图书馆的规模。
学堂这个活动的设计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来说,流于形式。我每天上午第一节都有课,马上是期末考试,送女儿就会错过上课,给女儿请了明早的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