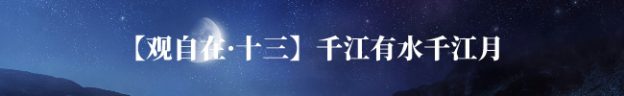昨夜枕边书,原本要读的是姜乙译的黑塞《荒原狼》。让我拿起这本购于也闲书局的作者签名本小说不是因为作者黑塞,也不是因为译者,而是一翻开的《出版者前言》里,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带着两箱行李和一箱书搬到了“我”姨妈家的阁楼。“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一箱书”、“阁楼”,让我想到自己。于是在等花卷洗漱的时间里,趴在床上,才翻不到五页,就差点睡着了。看来与这本书的缘分还不到,就去换了尼采的《教育家叔本华》。这本书仍然不太好读,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是在翻译上,当然也有可能翻译已经非常出色,只是原文即是如此。匆匆翻过,放下。人生很短,值得读的书很多。并不是每一本好书都与自己投缘。所以,读书在我就是读自己喜欢读的就很好,这样的阅读才是享受。想起昨天中国史1班的课上,给学生建议的“三个保持”:保持呼吸和进食,保持阅读和写作,保持思考和批判,否则人生不值得。
以后的人,将会特别反感研究这一时代的遗产,因为统治这一时代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被公众舆论控制着头脑的貌似的人。所以,我们的这一时代,对于将来的某一后世来说,或许是最黑暗和最不为人知的,因为这一时代有可能是历史长河中最非人性的。
如果一个人,如果他不愿意从属这芸芸众生的一员,那他就只需要不再懒散、随便和得过且过地对待自己;他就需要听从自己良心的这一呼喊:做回你自己吧!所有这一切,你现在所做的、所欲望的、所认为的——这些都不是你。
年轻人就带着这样的问题回望生活吧:你到现在为止真心爱过什么?是什么提升了你的灵魂?是什么征服了你的灵魂,同时又让其感受到了幸福?你就把你所敬重的那些东西一一排列在你的面前,或许他们就会以其本质和次序,向你给出某一法则,某一有关你的真正自我的根本法则。因为你的真正本质并非隐藏在你的内心深处,而是高高的在你之上,或者起码在你习惯认为的你之上。你的真正的教育者和塑造者,会让你知晓你本性里面原初的和根本的素材构成——这些东西,从根本上无法教会也无法训练而成,总是难以捉摸、收到束缚和扭曲。你的教育者,除了能够成为你的解放者以外,别五其他。这就是一切教育的秘密。真正的教育就是解放,就是施予光线和温暖,就是夜雨的润物细无声,就是模仿、敬畏和顺应大自然。不要欺骗任何人,更不要欺骗你自己。喜悦别人,智慧自己。
尼采《教育家叔本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1版,2017年8月2印。总阅读量第1420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