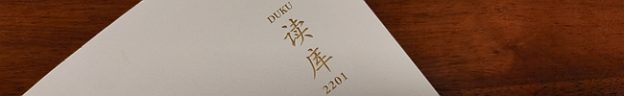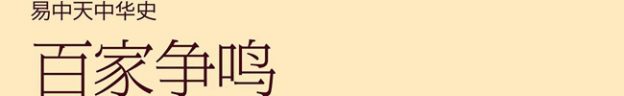每天上午在太座和两个娃出门后,洗碗、洗衣服、吸尘结束,开始学习。
上午三个一小时,一个小时英语课的听说读写;一个小时古诗词课,读、背和对注解学习一首王维的诗;一个小时佛学课,读佛经,学佛教史。下午是整个的自由阅读时间。
王维一首《李陵咏》,一百个字,从“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到“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无尽的无可奈何。王维十九岁作《桃源行》中“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句,与四十岁作《终南别业》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竟相呼应。另《桃源行》中“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似也是我生活环境的写照。
这两天下午的阅读是三刷也闲谈周六要进行的《战争与和平》相关章节。如果其它世界文学名著和历年的各种文学奖获奖作品都是一个个世界,那《战争与和平》就是一个宇宙。这个宇宙里面没有哪一粒尘埃是无用的,没有哪一句话是可有可无的,每一句话都有一个或多个远或近的因,也都有一个或多个远或近的果。因果交织,各色人等在里面生死浮沉。
Isaac在微信约了几次,说想聊聊,我说发邮件吧,写作能训练思维和表达,只有写下来的东西,才是你真正有的。写得清楚,思维就清楚,表达就更清楚。
晚饭前收到Isaac的邮件,说“亲爱的导师豆哥你好”,洋洋一千六百余字,说了他在读《冰与火之歌》原著,他与AI合作的小说遇到的问题,还有读到的一段对教育的看法。我晚上回复说——
“虽然一直以来都是待读的书太多,时间不够,但最近总觉得时不我待,所以时间和精力有所调整,尽量少使用社交媒体。用邮件的好处,是可以一次性在一个完整的时间段内就所有问题进行交流,而不是像微信那样时时刻刻东一句西一句好像聊了很长时间,但其实信息非常有限。我一直都在想卸载微信。
“AI写作目前还比较‘低级’,我估计未来两年内,AI的写作能达到一个熟练的网络爽文写手的程度,但要达到真正的文学的程度,还需要多两年时间。我相信,AI在未来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和终身的学习伴侣。
“关于教育,从这个词诞生的那时起,就是各说各话的。我猜每个教育中人都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试图定义什么是‘教育’或什么是‘好的教育’,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困难的,因为人人生而不同,所以就不会有适合每个人的教育(尤其要警惕那种以别人的错误来证明自己正确的缺乏常识和逻辑的教育从业者,因为我们讨论过多次,别人的错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就像1+1=3这个错误不能证明2+5=8的正确)。我觉得,终极的教育,或者说教育的根本,就是自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