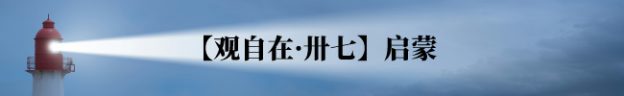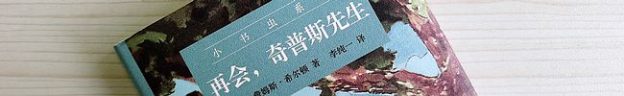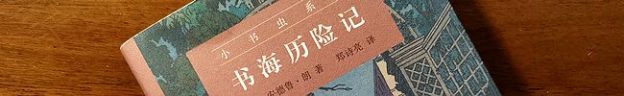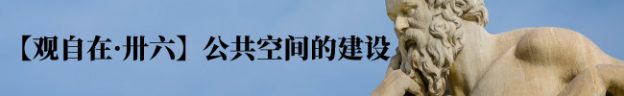语文3班,王孟诗比较番外篇,孟浩然的诗选了《夜归鹿门山歌》、《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建德江》、《过故人庄》四首;王维的诗也对应选了《山居秋暝》、《使至塞上》、《竹里馆》、《终南别业》四首。在讲了宋人魏庆之、明茶陵诗派代表人物李东阳、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明学者胡应麟、清初的徐增等人对王孟二人的比较和评价后,说王维、孟浩然谁优谁劣,历来众说纷纭。本番外篇,在比较,而优者劣者,全在于比较者的自我分析,我的比较分析也仅只是粗浅的个人看法,目的在于引发思考。这个内容有些超出了大家对诗词的理解和表达范畴,所以互动不如以往。
中国历史1班,从“烽火戏诸侯”中褒姒的经历,讨论中国历史中对女性的评价是否尊重和客观,玲的女生视角尤有说服力;从姜小白(齐桓公)的逆袭到曹刿论战,讲春秋时期战争的礼仪。
中国历史2班,在阅读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五章文本后提出问题:“周朝实行分封制,秦朝实行郡县制,汉初为什么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就此展开讨论。“历史天才”的分析和观点颇为独特,“地理天才”似乎对这样的话题略感沉闷,昏昏欲睡。
大家的4月阅读简报,六水大人的极佳,条理清晰,表达清楚,一次获得两个“A”。有三位同学没有按照要求用单独的本子作阅读简报,原因为“我以为……”,视为未按要求完成作业。“不要你以为,也不要我以为”我说,“谁以为都没用,因为有规则有要求,没有人可以凌驾于规则之上,大家都按规则来。”
将5月阅读推荐的书名和推荐语打印出来,贴在各位学生的本子上:
龙应台《野火集》
苏格拉底那个老头子被判了死刑之后,不愿逃狱,他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不错,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个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聂荣庆《菌中毒》
每个云南人都有自己吃菌中毒的故事——有人看到挂历上的黄果树瀑布动起来了,觉得水珠溅了出来,砸到了她脸上;有人看到朋友在说话时,头上出现了中英双语的字幕;还有人在家里看到了活的变形金刚,打电话叫朋友一定要来家里看,不然就绝交,朋友来了,这位中毒的先生打开盒子,展示“正在睡午觉的变形金刚”,朋友看到盒子里躺着的,是一个插线板……
可能是因为鼻炎,这两天昏昏沉沉,脑子不清醒。一天没打乒乓球,午饭后趴在桌上眯了20分钟,没参加飞盘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