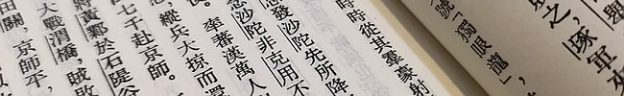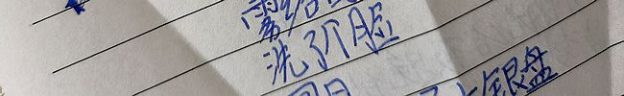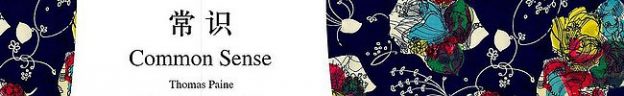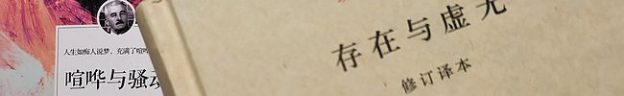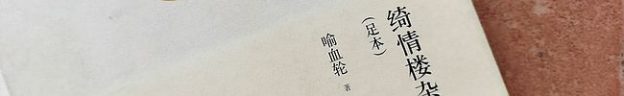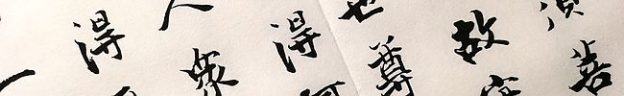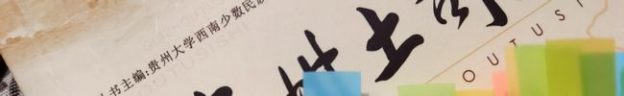/前夜读完拉尔夫·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总结下来,大致就是四句话:学校应该达到哪些教育目标;提供哪些教育经验才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怎样才能够有效组织这些教育经验;我们如何才能够确定并评估这些目标正在得到实现。
/昨夜枕边书,钟书河《念楼学短》(上下卷)读了上卷半本,几百篇文言文,分类、选文都相当精当,钟书河的解读,时代感浓烈,但跳过即可。强过很多现在市面上的所谓“大语文”读本太多。
/几年前,有次参加某公益组织的中学生读书活动,在黔南某县重点中学,大家轮流作阅读分享。轮到该组织一位多年的小学语文老师志愿者时,她躲开了,说自己已经好多年没读书了,不知道分享什么。我当时在心中吓掉了下巴——最可怕的事,是不读书的人在教书,不写作的人在教写作。
/凌晨,雷电交加,风雨大作。女儿害怕,在床上捂着耳朵,闭着眼睛叫爸爸。我把床头的书搬到地上,腾出地方给女儿,她说爸爸你这间好吵,然后一觉到天亮。起床,数数地上的书,二十六本,又搬回床头。
/周五,小学部负责人问我下学期小学三至五年级文言文课的内容规划,我说文从从半文半白的民国老课本开始,诗从《诗经》的《关雎》和《桃夭》开始。周末这两天,捋了捋自己对小学文言文课的理解和每节课的内容设计。
开设文言文课以来,每节课都有练字、古诗词“飞花令”和文言文篇目的学习。在我看来,这是一门“考古”的课程。因为:
写字这种行为和记录、表达方式,将从日常生活中慢慢消失,最后将像绘画、音乐、书法一样成为一种艺术家的艺术行为,或像手工银饰制作、雕版印刷一样成为一种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手工技艺和一个小群体的兴趣爱好。
古诗词和文言文,在教材里从一年级到高三,必背古诗词近三百首,文言文约一百篇。我们大多数人在离开校园后,终其一生都不会再学习新的古诗词和文言文,并会忘掉百分之九十在学校已学过的内容。那学习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快递小哥比别人多会背一百首古诗词,也不能比别人每天多送一百个包裹,多赚一百块钱;老板也不会因为一位项目经理比其他经理多会背一部《论语》而给他增加一百万的年薪。而什么培养审美、什么熏陶这样得话更是苍白空洞毫无说服力。
有的学生或家长人认为学校里有些科目或有的篇目不值得教授。我的办法是,先提供学生所需,再由学生则选取他们所爱——例如本学期五年级的《论语》讲了一半,学生要求讲语文课本高二必读篇目《庄子》的《逍遥游》,于是课程内容就调整为了《逍遥游》。教育,很多时候在我看来和医学一样,是一种什么都不确定的科学和什么都有可能的艺术。同样的教材、同一所学校、同一批老师、同一个班级里,每个学生都不会成为同样的人。如果这不能发展成为兴趣爱好或研究方向,这将是多数人一生中唯一接触古诗词和文言文的机会,这是一种人文教育可能性的尝试。而最终留下多少碎片,是哪些碎片,人生,就是从这些碎片中开始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