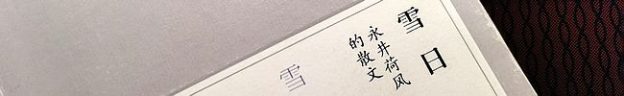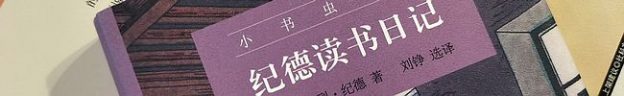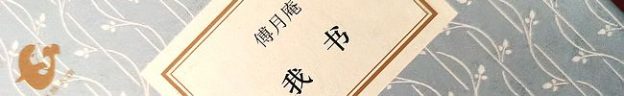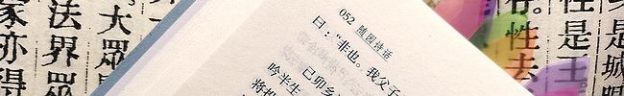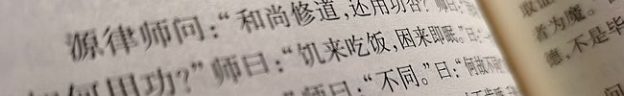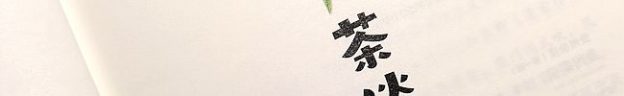“两日读毕。喜欢永井荷风的文字,胜过川端康成、村上春树和泉镜花的。”我写在永井荷风的《雪日》的扉页。只是因为文字细腻又唯美,在这个晚来天欲雪的日子读来,每每于我心亦戚戚然,所以薄薄一本16万字的散文集竟然读了两日。从照片上看,永井荷风真是又丑又蹙缩。可能是因为外表和内心都平庸,于是将外表搲去一块给了内心的缘故罢。
“我只是个避世隐居之人。日复一日,我考虑的只是如何不抛头露面,不花费金钱,悠闲随意地生活下去。”(《晴日木屐》)于我亦然。
“正如浮世绘中所描绘的那样,小巷如今依旧是贫苦民众的栖居之所。那里潜藏着从阳光普照的大街上无法得知的百态人生;蕴含着清幽之所的虚缈之美;享受着隐居生活中那份远离世俗的宁静;沉淀着从失败、挫折、穷迫中修得的慵懒与无拘无束的闲逸恬淡;展现着赌上性命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的非凡勇气。小巷虽然短小、狭窄却如这般多姿而富有情趣,犹如一段段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小巷》)
“狂暴的寒风骤然停歇,整个世界顿显清冷、静谧。悠悠点燃一支蜡烛,照亮桌上的晚餐,正待举筷之际,‘啌’的一声钟鸣无比清晰地传至耳际,满含了悠远、纯厚、深邃……令人不禁追寻钟声传来的方向。却只见夜幕初降的天空,寂寞的金星独自闪烁,一轮新月掩映在枯枝中散发着清冷的光辉。”(《钟声》)悠远之美。
“平时伏案读书写作累了,便信马由缰地踱步到神社院内,就如同在自家庭院一般,一个人在院子里望望飞鸟,看看许愿牌……什么也不想,悠然徒步。”(《坡》)亦我所欲也。
“在我看来,比起战死沙场的勇士气概,留在家中抚养孤儿的老妇和孤零零地往炉子里添柴加碳的老翁们的内心更加可怜。与那些愤世嫉俗、慷慨赴死的人相比,被迫随波逐流的人更加值得同情。”(《便携秃笔》)
“长吉心想:她也该来了吧,于是专注地望着桥对面。最初从桥那边走过的是一位穿着黑麻僧衣的和尚,接着是一位承包商模样的男子,他穿着紧腿裤和胶鞋,酷酷地将后衣襟撩起掖在裤带上。过了一阵儿,又有一个提着布雨伞和小包袱的穷妇人粗鲁地踢踏着矮齿木屐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之后,再等也没有人经过了。长吉无奈地把疲惫的双眼移到河面上。这时的河面整个都变得明亮起来,涌动的云峰消失得无影无踪。今晚的月亮应该是七月中旬的满月吧,圆圆的月亮略泛红光,爬上了长命寺边河堤上的树丛。天空被映照得如镜般明亮,堤坝和树丛被背后的月光衬得越发显得漆黑。天空中只有那颗太白星依稀可见,其他星星均被明亮的夜空藏了起来。天边那条如丝带般长长的浮云间透出耀眼的银光。很快那轮圆月便离开了树丛升上天空,于是岸上沾满夜露的瓦房屋顶,以及被水打湿的木桩、被涨潮的河水冲到石墙下的水藻碎片,还有船身和竹竿都按上了皎白的月光。长吉映在桥面上的影子也越来越清晰。恰巧此时又有一对卖唱的男女路过,他们说着‘你看,月亮’,驻足观赏了一会儿,便向山谷渠岸边走去。这二人走到岸边成排的小屋前若有所指般地开始唱道:‘书生靠着栏杆呀——’不过,也许是意识到没人会给钱吧,两人没唱完就步伐匆匆地向吉原堤坝方向走去。除了一般幽会恋人常体会到的各种担心与苦等时的焦虑外,长吉此时不知为什么还感到一丝悲哀:阿丝和自己还有没有未来?”(《隅田川》)美妙的等待。
书架上,还有一本初版于1902年的永井荷风成名作《地狱之花》。看,还是不看,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