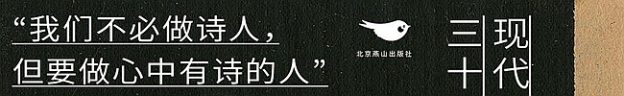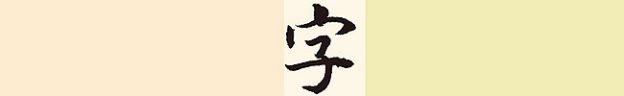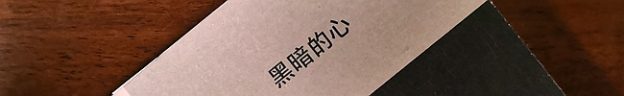“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很难找到天然的环境,连大寺院周围也都沦陷了。不止我们的环境被污染,就连寺院本身也成了高级消费的场所。寺院不像寺院,我们这种习惯食用斋饭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变得很碍眼。”(《山间独居》)寺院大多已成为宗教地产或文旅项目,我这三十年里,竟然没有见到过一位看上去能让人心生恭敬并忍不住亲近的出家人。
“把拥有的物品减到最少,让心灵得到升华,成为宇宙生命的一部分,这便是清贫。清贫是一种节制的美,是人类的基本美德……抛开执念,放弃一切,我们才能真正听到心灵的声音。全部清空时的那种纯粹的饱满感,就是净土;舍弃一切,从束缚中解脱时,那纯净的圆融感,便是极乐。”(《禅思小径》)唯独在书上面,我做不到舍弃。只想买了再买,是不是就感觉书架上又缺了一本必须要拥有的书。这是我的执念。
“幸福不在于拥有了多少,而在于摆脱了多少。”(《智慧抉择》)我现在住在距离省城和县城都十几公里的乡下,不用社交,微信朋友圈的“朋友”也越删越少,反而觉得距离“幸福”越来越近了。
“菩提自性,本来清静,只是由于散乱,把心思放在不必要的地方,没有散发出光芒而已。参禅也是行,不管是参禅还是念佛、念经都是一种行,磨炼的行。通过行来释放原本心灵深处的光芒,坚持以行度日,结果就是开悟。”(《洞视内心》)
“有些信仰虔诚的人,要比没有信仰的人还狭隘,有时他们无法学习新知。”(《少拿多得》)看到这句话,我想到刚读过的五明佛学院副院长慈诚罗珠堪布的《我们为何不幸福》。在豆瓣给这本书的短评只有六个字:堪布要加油啊。
法顶禅师《山中花开》,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年1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621本。
公入寺烧香,主事祇接。因观壁画,乃问:“是何图相?”主事对曰:“高僧真仪。”公曰:“真仪可观。高僧何在?”主事无对。公曰:“此间有禅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执役,颇似禅者。”公曰:“可请求询问得否?”于是遽寻檗至,公睹之欣然曰:“休适有一问,诸德吝辞,今请上人代酬一语。”檗曰:“请相公垂问。”公举前话,檗朗声曰:“裴休!”公应诺。檗曰:“在甚么处?”公当下知旨,如获髻珠。(《《五灯会元》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