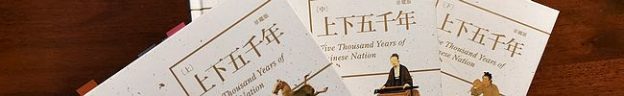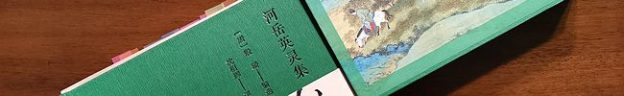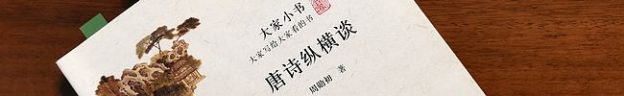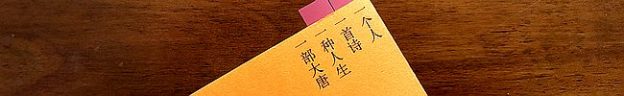把1186页,74.1万字的,林汉达、曹余章《上下五千年》又大致翻了一遍,随机挑了其中七八篇故事认真读来,亦有新知,觉得把这套书作为中国史启蒙读物以及语文课外阅读材料都合适。又随便翻开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正好是“王莽新政”,让花卷用几分钟读了这两页内容后告诉我这一节讲了什么,她基本能读懂,有一两处需要我补充讲解。这样一来,新学期初中中国史两个班的教材,就算是基本确定了。
以低年级学生为主的低阶班教材为林汉达、曹余章的《上下五千年》;以高年级和语文程度较好、对历史比较有兴趣的学生为主的高阶班,教材为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林汉达(1900—1972)原准备基于“对新语文的尝试和旧故事的整理”,写一套包括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故事集,但生前只写到东汉以前的部分。东汉至清鸦片战争前的历史故事,由曹余章(1924—1996)在1981年续写完成。现在看到的《上下五千年》这个版本,按历史顺序,从远古神话传说时代至清鸦片战争前共262个故事。
谈历史就不能不涉及到观点问题,这也是我选择初中历史教材最为头疼之处——很多历史启蒙读物,不是观点先行就是以偏概全,要想找到比较不那么感情用事且又行文较为顺畅甚至优美的,可作为通史或断代史教材的,实在是不容易。
作为一套故事化的历史启蒙读物,在涉及历史观点这个问题上,《上下五千年》的两位作者采取的方法是我非常认可的“尽量不发议论,少做分析;有些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判断。”在运用文献时“不用现代的观点去修改史料,故事中人物的活动、语言,基本上都是按照原来的历史原样写的”,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也不轻易做全盘的肯定或全盘否定”。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历史学习,也才能接近作为我所任教中国史的教学目标,即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说的:“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之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推诿于古人。”
林汉达、曹余章《上下五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1版,2022年1月9印。总阅读量第1417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