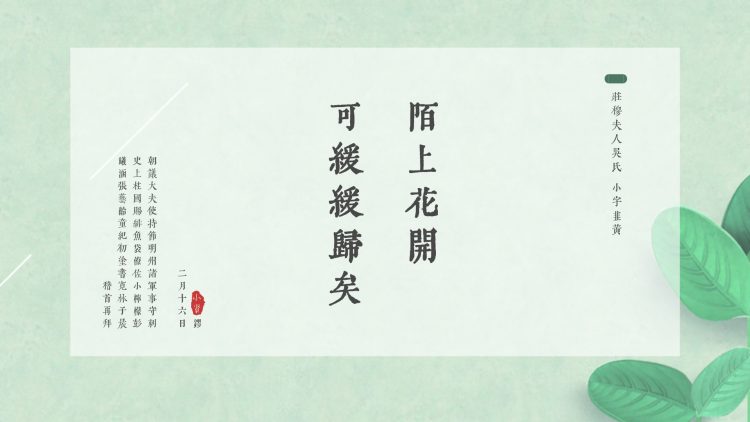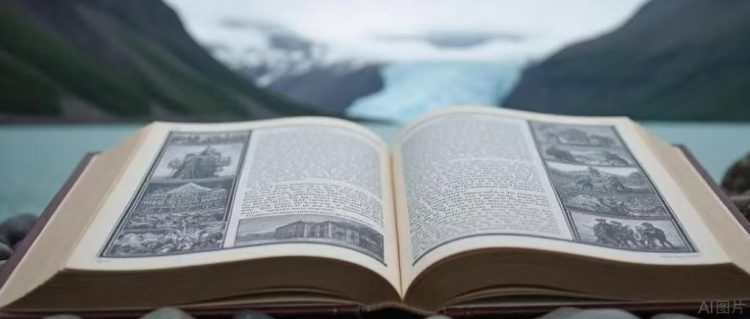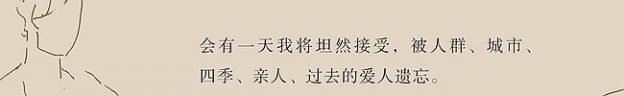早上出门去地铁站,一路小雨濛濛,想起《边城》里“雨落个不止,溪面一片烟”,就突然想读沈从文。
在北京路上的省图书馆南馆看了45分钟的《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中间想去借一本沈从文,星期四看完还,又嫌重新办卡麻烦,作罢。
和Isaac在也闲书局,他说起国足如果再赢两场就能小组晋级,我看了排名,倒数第一,净胜球比小组第一的日本队少30球,还是老样子。我说小组赛国足和日本踢,只能用5-3-2的阵型了,因为这个阵型的目的只有一个:球是肯定要输的,只努力尽量少丢几个,不要太难看。结果已经对战了,Isaac给我看结果,0:7。还是老样子。看来只有年轻人还对中国足球抱有希望。也算是好事一件。如果不是Isaac,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聊足球。
Isaac给我看了他整理的,欧元各面值纸币上的人物和建筑资料,欧元所展现出来的其成员国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一个了解欧洲甚而世界的窗口(虽然感觉有点市侩)。我相信一定有收集各版本欧元纸币和硬币的藏家,如果把这些硬币在一面墙上拼成一幅欧洲地图,地理、历史、文学尽在其中。实在是有趣。世界那么大,我有点想去看看了。我和女儿也有一个小目标,就是看100座博物馆,收集100枚博物馆的纪念章。目前完成了四分之一。
从博物馆聊到游学,看Isaac的西北游学1.0方案,内里只有博物馆和图书馆,我说那你还不如来一个博物馆之旅,先从三大博物馆开始。台北暂时不打算,北京他去过了不想去,南京倒是没去过,我说那南京博物院如何?南京,六朝古都,历史厚重、藏品丰富,常展特展几天都看不完,有好吃的,好玩的,逛了博物馆再去逛古玩地摊,带几件赝品回家把玩,多快乐?!他,就这么动心了。于是游学目的地先从华南调整到西北,现在调整到了华东。
共读《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Isaac在读书笔记里敲了这样一个结论:查理五世对欧洲的统治虽短暂,但其遗产——西班牙的黄金时代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直接塑造了17世纪“三十年战争”的格局。我问查理五世与西班牙的黄金时代、神圣罗马帝国是什么关系,他又是怎样塑造了“三十年战争”的格局的?于是在墙上的巨幅世界地图前,苏格兰、英格兰、尼德兰、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新教与旧教(天主教),看Isaac指点江山纵横捭阖,他不是在背书上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在重新呈现历史,好不享受。我就是时不时追问个“为什么?”,然后他又会打开历史的另一扇新门。最后在我们的饥肠辘辘中,结束于西班牙圣地亚哥朝圣之路上,作为朝圣路标和朝圣者完成圣地亚哥之路证明的扇贝。
如果Isaac的历史学习是一次就像圣地亚哥朝圣那样的长途旅行,我们的每一次讨论,就是那个朝圣者扇贝上的一个个路标,最终他会指引自己去往心中的圣地。
Isaac的阅读,除了《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还有英文原版书、芬兰作家阿托·帕西林纳的代表作《遇见野兔的那一年》,我说这个阅读量很大,来得起不,他说还好。还好就好,安逸。大量阅读后我们一起闲谈讨论,他带着一堆“是什么”来,又带着一捆“为什么”回去,在历史中探索,在现实中发现,我觉得这才是“学历史”。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成就的过程,每一位学习者都是走在朝圣路上的新圣人。
这个月我们每次讨论都会提及哈布斯堡,好想看卫克安《哈布斯堡王朝》、彼得·贾德森《哈布斯堡王朝》和杰弗里·瓦夫罗《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但他们最终还是输给了沈从文。离开也闲书局时,我带走的是沈从文别集一种《阿黑小史》。在回家的地铁上读了四十多页,觉得还是不如《边城》好,没有那么清澈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