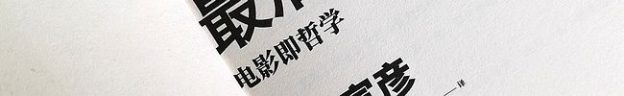我的豆瓣观影记录,从2006年11月到现在看过了1842部影/剧。如果算上剧集,观影量3000+。按平均一部时长1小时计算,这18年里,我有125天的时间是在看各种电影,平均2.19天一部。看电影和读书对我来说,不只是娱乐,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从中看到的不只是过去和想象,还有现在和未来的真实。
大林宣彦(1938—2020)认为,电影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娱乐方式,能够简洁明了地传达一些哲理,使它们不必埋没在历史的风沙中。但电影的本质,并不是在娱乐作品中强插哲理,而是要基于哲理来创作娱乐作品。人类自己创造的哲理,也许确实只有一半是正确的,还有一半是错误的,但即使是错误的,人类也应该拼命地表达。要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当下正在发生什么,才能不随波逐流。就像犹太人,他们知道世界是不美好的,因为他们自身体验过世界的不美好。他们也知道世界和平是个大骗局,但是相信这个骗局说不定有一天就真的能实现。这就是“美好结局”的思想。相信电影的力量,即使每次只有一点点,也要将对和平的向往留在世间。即使这个过程再慢也没有关系。现实世界并不和平,并不快乐,但要相信有一天它会变得快乐又和平。电影的职责是将这个“谎言”告诉大家,然后用“谎言”背后的真诚让大家相信。这就是电影的美好。
如果这是你人生中的最后一天,你会讲述什么?日本NHK电视台大受好评的纪录片《最后的讲义》完全版四种之一,大林宣彦《最后的讲义:电影即哲学》,海峡书局2022年5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47本。至此,《最后的讲义》完全版四种全部读毕,西原理惠子《最后的讲义:女孩一生中最需要知道的事》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