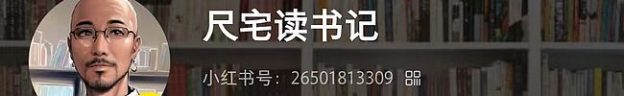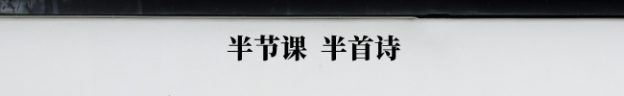【语文】
本学期只有四个教学周就结束了。最后一周是教育局统考,倒数第二周是我们学科的期末口试、笔试评估,上课就只两个教学周。与熊猫老师商量下来,语文这两周都合班上,重难点我来讲。
今天语文课,熊猫老师讲了刘禹锡的《望洞庭》、《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和《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三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和《陋室铭》我明天讲,“刘白”这个主题的重点在白居易的《琵琶行》。
六水大人的课题作业,进步之速如有神助,才不到两个六周的时间就从“F”直升至“A”,不论是肉身还是思想在一个自由和尊重的环境里都能得到恣意生长。
吴在期末到来之前,终于稳在自己的“舒适区”——不论软笔簪花小楷字帖还是每日一记和课题作业,都是“A”。下一步要鞭策的就是让她把“舒适区”扩大到历史、地理、英语和数学诸学科。
【中国历史】
初中从六至九年级的所有学生,都在中国历史两个班。
今天中国历史课,公布了语文和中国史期末评估的准确时间和确定内容:
7月1日提交语文期末笔试《AI时代的教育》和中国史期末笔试《我的2024》;7月3日本学期第三个六周口试飞花令,4日“荣耀之战”——飞花令学期总冠军、学年总冠军PK。
我说:“诸位还有两周的时间来完成这两项期末课题。所以这两周的课不讲新内容,你们要利用这两次课的时间开始构思,可以讨论,有不清楚的可以问我,也可以提出你的想法,或许听取我的建议。”
“要写多少字啊?”第一次参与期末评估的子阳君问。
“字数不限。你用五个字说得清楚也可以,你用洋洋洒洒五千字也行。”
“那我多写点是不是评估等级会高一点?”同样第一次参与期末评估的子乐君问。
“不是的,不是的,字数多少和评估等级是没有关系的”,吴抢着说:“你就像我上次课题作业写了一千多字,结果因为犯了‘低级错误’只拿了‘F’,所以豆总看的是质量不是数量。”不愧是老生。“对我来说也有类似的惨痛教训啊哈哈哈……”花卷附和。
“豆总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呢?这个学期学的都是诗,我可不可以把这些诗串起来表达我想表达的?”吴接着问。
“你说呢?如果想听我的建议,我倒是觉得你可以从月亮回顾一下这个学期……”
“可以了,豆总,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了,可以不用说了。”吴赶快掐断我的话。
“豆总,你觉得什么是‘历史’?”大魔王问。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但我不会回答你,因为那是我的答案,不是你的。你要去找到你的答案,那时你来找我,我再告诉你我的答案,这样我们都能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
“豆哥,对我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六水大人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期末评估,有点懵,可以理解。
“可以是编年体,可以是传记体,可以是以事件来推动的,也可以是采用以某一时间为节点前后比较的,还可以是以关键词为脉络的方式。例如……”我正好看到她已经在本子上开始的框架,“这样就很好啊!”
“那我可不可以用诗歌来表达?”也是第一次参与期末评估的子琨君问。
“为什么不呢?字数不限,体裁不限。这是你们的2024,不是我的2024。不过歌的话,那可是要用唱的哦。”我说。
“是诗,是诗,诗词,不是歌。”子琨君说。
“可以啊!但我还是觉得用歌更好。”
“好的豆总,你的建议我会部分听取的。”
“那我画一张图来完成《我的2024》。”同样也是第一次参与期末评估的张丞相说。
“完全可以,但要有读者意识,不能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
“什么是读者意识?”
“你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幅画、每一首诗、每一个字,都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看的,而是写给这个小小星球上的每一个人看的。要通过你的作品传递你的思想。”
午饭后,大魔王来办公室找我:“豆总,关于中国历史期末评估,我想弄清楚什么是‘历史’和‘现在’这两个概念,因为¥%&*#@¥%……。”
“多好嘛。如果你能弄清楚这两个概念,这可能就是你2024的最大收获。在现在这个阶段,不要在意什么标准答案,历史也不是要去背那些时间、人物和时间,而是首先要建立自己的历史观,也就是对历史的理解和方法,这个才是豆总我历史课的终极目的。”
“好的!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