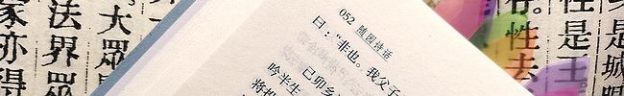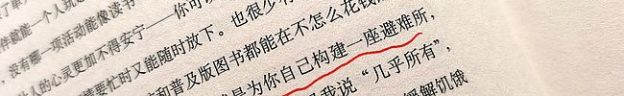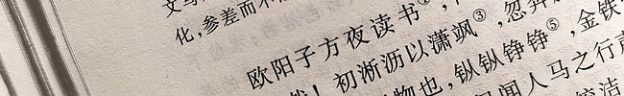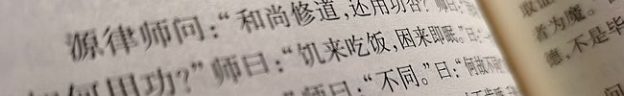防护服挨家挨户敲门让去做封控第七天来的第四次核酸检测。在露天停车场排队被捅完喉咙,立马就有防护服拿着扩音喇叭喊:“做完核酸请立即回家,不要在外逗留。”看着一路刚被驱赶出圈门马上又被驱赶回圈的羊群,突然就想起早些年看过的一部老电影《卡桑德拉大桥》。
整天都有防护服骑着电动车喇叭里单曲循环“静态居家,禁止外出。”在小区里四处巡行,好咆烦。下午实在是躁郁,在空无一人的小区里大步流星暴走五公里汗湿T恤,才觉得微微气顺。晚饭后花卷和闺蜜在花园里玩到快九点才回家,她说玩得很开心,我就放心了。花卷洗澡时,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花果园有人跳楼的视频,心情不佳。
闭门夜读袁枚《随园诗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7月简体横排版,无译注,但好在是全本。明清小品文就算无译注,基本上也能读个七七八八,就算少量用典难查,也好过市面上各乱译版本。之前就读过一巨坑的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9月版《随园诗话译注》,只是选译又不注明,而且译文的错误还不少,部分译文竟然只是把原文抄一遍。
今天读来几则有趣:
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呵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
诗贵翻案。神仙,美称也;而昔人曰:“丈夫生命薄,不幸作神仙。”杨花,飘荡物也;而昔人云:“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有一春忙。”长沙,远地也;而昔人云:“昨夜与君思贾谊,长沙犹在洞庭南。”龙门,高境也;而昔人云:“好去长江千万里,莫教辛苦上龙门。”白云,闲物也;而昔人云:“白云朝出天际去,若比老僧犹未闲。”“修到梅花”,指人也;而方子云见赠云:“梅花也有修来福,着个神仙作主人。”皆所谓更进一层也。
贫士诗有极妙者。如陈古渔:“雨昏陋巷灯无焰,风过贫家壁有声。”“偶闻诗累吟怀减,偏到荒年饭量加。”杨思立:“家贫留客干妻恼,身病闲游惹母愁。”朱草衣:“床烧夜每借僧榻,粮尽妻常寄母家。”徐兰圃:“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说邻家午饭香。”皆贫语也。常州赵某云:“太穷常恐人防贼,久病都疑犬亦仙。”“短气莫书赊酒券,索逋先畏扣门声。”俱太穷,令人欲笑。
苏州黄子云,号野鸿,布衣能诗。有某中丞欲见之,黄不可,题一联云:“空谷衣冠非易觏,野人门巷不轻开。”《郊外》云:“村角鸟呼红杏雨,陌头人拜白杨烟。”《上王虚舟先生》云:“两晋而还谁翰墨,九州之内独声名。”皆佳句也。子云于城外构一草屋,客至,则具鸡黍,夜留榻焉。父子终夜读书,客叹其好学,曰:“非也。我父子只有一被,撤以供客,夜无以为寝,故且读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