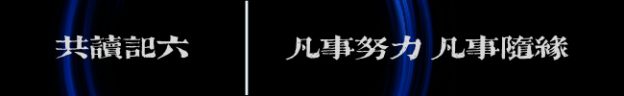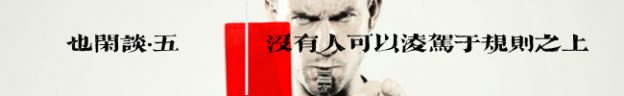1992年,华纳唱片发行林子祥专辑《影视金曲16首》,其中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插曲《长路漫漫伴你闯》,在1993年获得第1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
30年后,在也闲谈,想起这首歌——
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你到天光/同花讲古 同鱼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出棍重出埋枪/话之江湖点鬼样/长城游罢游长江/一生陪你做逍遥帮
只是我和也闲书局的局座大人秋蚂蚱不会(敢)拉帮结伙,只是想做个“汉堡王”。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我说了十几年。今天又再说了三遍。重要的话说三遍。
今天开始切入了写作。上午,在切下去之前,每一位学者,每人三分钟,分享查找到的,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宗教、民族对“人类的起源”各自不同的故事。从不同故事诞生的不同地理位置来看这些故事的异同。在哪里闲谈,我都离不开大地图,因为在我看来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就是基于地理的发现而展开的,而伴随人类文明的战争,其本质就是对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资源的争夺。
分享结束,“老伙伴”,五年级的老徐问小黎我是不是可以恢复我们之前的“文字游戏”。这是只有我和老徐、企鹅才知道的“传统”——不用一个字词及其近义词、反义词,写三句话,让别人能读出这个字词所要传递的信息和感受,就像文字版的比动作猜词语。由此引出问题:“写作”是写给谁读?
各位学者将阅读对象分为了两类,一是自己,一是别人。自己又细分为自己的眼睛、心、肺等;别人包括同学、老师、家长、毛豆(这个特殊的一类让我感到自己并不孤独)、动物、神等。没有想到的是,超过一半的学者明确表示不喜欢写作文,原因有很难凑到要求的字数、写的是规定的题目等原因。
“在我们这里,并不把作文归为写作,更不会把它视为天花板,因为它最多只是脚底板。”我说。“并且,也没有字数要求。如果你能用5个字表达清楚,很好;如果你觉得需要1500字才能表达清楚,很棒。字数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没有表达清楚。什么叫‘表达清楚’?就是除了写给自己的,例如日记这样只需要自己明白的私密写作,其他所有的写作都应该是公共写作,要有读者意识,要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因为你的每一句话,每一篇文章,都是为这个小小星球上的‘别人’,也就是世间万物所写。‘表达清楚’就是能将你的感受、想法传递出去,而接受者能够理解并能作出回应。因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是……”
“毛豆说的!”有学者说。
“这个……此时此刻确实是我说的,但我不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学来的。这个人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名字是……不告诉你们,感兴趣的话自己去查吧!”写作的门就此打开。
中场休息,果盘上桌,“请大家好好品尝这些水果,在我们下一个环节开始,各位要用三句话来描述自己吃到的是什么水果,它给你的是什么感受,这个描述要用到五感中不低于两种的感觉。”写作就这么开始了。
分享环节,有颜色,有声音,有画面,有表演,五彩斑斓,想象力的丰富程度和厚度让每一个分享都是一个经典片段。“各位,这就是最好的写作!写作不是作文,是感受的表达、情感的传递和思想的碰撞。”所以在这个长假结束后的下一次也闲聚会,各位将展示他们的课题写作。
“我和秋蚂蚱老师会交叉拜读各位的作品。我们没有批改,只有欣赏。欣赏各位的创作,并会在文后留言,我们将通过文字来交流。”
下午的闲谈,是我和局座秋蚂蚱大人“两个年龄加起来超过一百岁的老头”的“汉堡王”组合与高年级学者对谈。我们从格陵兰岛到冰岛,从黑船事件、日俄战争到甲午战争,从大青龙旗、五色旗、福泽谕吉、李鸿章到古希腊怼王苏格拉底,从尼安德特人、元谋人、演化到AI、可控核裂变、氢的同位素、可控核聚变……但与上午相比,我们感到有一些吃力。这种吃力不是因为我们唾沫星子如月季花般四溅导致的脱水虚脱,而是因为高年级学者们总像是在完成规定动作,不够勇敢,不敢冒险和主动探索去提出问题,激情不足。我理解,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在一个只有标准答案,要密切关注老师对每一个问题的权威判断——甚至是审判——的环境里,他们已几近失去了自我。我和局座想做的就是让他们重新找到自己,点燃自己,因为“就连人类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目前都没有定论,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和可能性,我们又怎么可能让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