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这些都好贵。我们这么穷,肯定买不起吧?!”花卷指着手机里一些知名日本手帐文具品牌的产品说。
“剔除了智商税的成分后,通常情况下,好东西都不便宜。”
“那爸爸你见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所谓免费的东西才是最贵的。”
“为什么?这说不通啊。”
“举个例子——封控时那些送上门的,让很多人感恩戴德的,里面装着两根萝卜两棵白菜和几个土豆洋葱的蔬菜包都是免费的,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嗯……自由!那些蔬菜其实是用我们的自由换来的。爸爸,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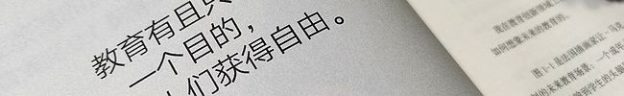

没有桂花香了。解封了,但小区的公共区域仍然看不到几个人,疫情之前开得好好的商铺,这封闭差不多一个月大多数的都开不起来了,门上的锁一直挂着。各行业和各行业的人都凋敝得不行。
在微信里给出国留学预备班的学生说,网课期间的作业安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书面作业,但各位要比以往更加仔细和努力去观察、感知当下,对看似合理的一切多提出几个为什么。正常上课后,也不会有什么像初中生那样的固定书面作业(除了每日字帖一页,没有的可以提前准备了)。在讲完已准备的《六祖坛经》后,我们开始读书会。每次课就是每人来分享自己正在读的一本书,并讨论。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想想这个学期,你要选哪一本细细从头读到尾。这本书,最好是跟你们所选的专业相关的。
我决定就陪读了。网课把课程计划弄得稀碎。
女儿前脚迈进家门,看见一条小蛇钻进弟弟脱在地上的鞋子里,吓得不敢进家。我用火钳把鞋子夹到花园,抖出一条通体脆绿筷子长的小蛇,倏忽消失在草丛里。太座和老爸说应该打死而不是放它走。我搜了两条发给太座,大概就是蛇为地龙,“青龙入宅”是兴旺之兆。
花卷肺炎住院,我陪护,靠门的床位。每天她抱一摞书,我抱一摞书,一人一天看完一本。不看书时闲聊,她说身边的朋友和每天发生的事总在变化,无法预测,也没有办法提前准备,更是不长久,感觉好无助。我说这就是无常。“无”就是没有,“常”就是不变,“无常”就是这世间没有什么是恒定不变的,除了无常;当无常为常时,也就无所谓常与无常了,就像没有黑就不会有白一样,或者黑就是白,白就是黑;就像你终究要独自面对生活,因为我们一家人也不可能一直在一起,爸爸妈妈迟早都会离你而去。
住院部的上行电梯里只有四人,我身后一对看上去大概三十四五岁的夫妻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孩。
“你看起来和别人不一样。”小孩子的父亲说。
“你说我?”沉默了两三秒,没听见有人给他回应,我回头问。都戴着口罩,看不出来谁是谁。
“是的。”
“有哪里不一样?”我笑。
“你看起来很淡定。”
“这个,我倒是没太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比较不担心会错过什么。”
“是因为这个吗?”他看着我手腕上的珠子。
“哦,或许和我是佛教徒有关吧,我不太确定。”我们在同一层出电梯,前后走进同一间病房,他把抱着的小孩放到了和花卷隔了两个床位的靠窗那个床上。
晚上翻的是MUJI BOOKS“人与物”系列文库本《小津安二郎》。这个系列的文库本装帧设计都很MUJI,深得我心,内容嘛,非常适合我这种不能坚持连续思考60秒但又不想不追随文艺者;美中不足,排版都自右至左竖排了,却不是繁体。
“相比故事本身,我觉得自己更想刻画的是,更为深奥的‘轮回’或‘无常’,诸如此类。”
“如今这世道人皆飘零,很多人也只剩下一颗坚韧的心了吧。”

上午听说东凤镇有两个阳性,恐慌比病毒传播的速度更快,不到中午,各大大小小的超市又被抢购一空。
晚上九点,大喇叭又在小区里喊去做核酸。太座已经带二娃睡了,我和花卷去到最近的核酸采集点,在露天地里两队乌泱泱从婴儿车里的婴儿到满头白发的老人排了几百人。我们从九点半等到十点二十,志愿者的回答还是条码“在路上”。这三个字让我就想到了“垮掉的一代”经典之作,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On the Road)。队伍越来越长,气温越来越低,回家睡觉。
回家路上,花卷问就这么回家,没做核酸怎么办。我说我们到了指定地点,等了近一个小时,做到了我们能做的就行了。
可能明天开始又要被“静默居家”不知道多少天了。这实在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祸——开始确实是“灾”。
灾,《说文》:天火也。指自然发生的灾难、疾病等不幸。所以说“天灾”而没有说“天祸”的;
祸,《说文》:害也。神不福也。人要是坏起来,连神也没有办法啊。

世事不堪,懒得写日志。一度开始动手删除数据库,关闭博客。但又想,如此不堪,怎么能不敲下来?多年后肯定会忘记诸多细节或记忆被人篡改装扮,留一个文本给自己,或许儿女也能看到。
开始时,我只是在五年级微信群里告诉学生和家长,可以把我的作业放到当天的最后一项来做。如果做完其它作业已经是晚上九点以后了,就可以第二天再做,只要在下一次课开始前完成就行。因为网课期间我一周只有两次五年级的阅读写作课,一次在周二,一次在周五。
后来我对六年级至高中的学生也作了同样的作业要求,不过与五年级不同的是,如果做完其它作业已经是晚上九点以后,就可以不用写我的作业,同时发一封邮件给我说一声就行。
我所在的乌当区算是部分解封了,但已封控21天的云岩区还在天天核酸中。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经历过非典封控,还算有一些社会阅历和磨难的社会底层人而言,十几二十天的封闭时间和空间,都是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更何况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再给他们施加任何压力。
今天,我在网课里和高中学生说,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休息,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身体的健康和好的心态,至于学习,就算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耗尽生命,你也学不完人类诞生迄今积累的知识,所以既然如此,有什么好着急的?每年世界上有近百万种图书出版,一个人终其一生也读不完这一年里出版的书,所以读过哪一本,没读过哪一本,从目前来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不要停的是阅读,要一直读,每天都去读点什么,读后要思考和提问,这和呼吸、进食一样重要。
今夜,再读《六祖坛经》。

心中郁结烦闷,足又不能出门半步,只好枯坐读书。
傅月庵散文集《我书》,海豚出版社“海豚书馆”系列第五册,2010年10月一版一印。
“小说,一如所有的书写,原始最终的目的,总期望能增益、丰饶读者的人生。”这个说法有点像我敲日志。不过我不是为了“增益、丰饶读者的人生”,我的日志读者就是我自己,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不把当天的事敲下来,很快就会忘记。这就像我常常回忆不起来我是怎样活到这把年纪的,如果人生是一次旅行,虽然没想明白这次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但至少还可以记录下旅行途中所见所闻的碎片。
“人与书的相遇,皆属缘分。偶然读到某一作者某一本书,因着他的思想,有所感应,一读再读,不知不觉便可能改变了一生的命运。”我没有过哪一位作者的某一本书打救了我,我是不停乱翻的书和作者们改变了我。也许是命运的改变,也许也还是宿命。
“文字像武器,练家子都知道,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文章写长易,写短难。此所以古人谈到文事,总以‘能删敢删’为高。”这一点和张大春在《文章自在》中“相对看去,短小之文,不好写,因为能调度的字句不多,唯求笔触精准而已。”看法一致。
海豚出版社“海豚书馆”系列104种,至今已淘到71种。就算一天读一本,至少也还可以读两个月。我就是伍尔夫随笔集《普通读者》中的那种普通读者——没有那么高的教养,造物主也没有赏给他那么大的才能。他读书,是为了自己高兴,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的看法。
下午看新闻二则:
18日晚,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刚为三荔高速重大交通事故向全社会诚恳道歉;
贵阳市三名干部因三荔高速客车侧翻事故被组织处理。贵阳市云岩区委书记朱刚,云岩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区隔离转运工作专班组长宋成强,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肖凌云被停职检查。
“停职检查”就像孩子闯了祸,拎回家拍了屁股两巴掌,然后道个歉,一副“都道歉了,孩子也教训了,你还想怎样?”的态度,难道关起门来教训一番,内部停个职休息一段时间,写篇检讨就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了么?想起《流星花园》剧中“F4”之一的道明寺那句台词:“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嘛?”
封控18天,终于在晚饭后解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