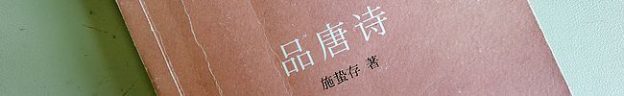“金石”这个词,起源很古。《吕氏春秋·求人篇》说夏禹的“功绩铭于金石”。高诱注曰:“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可知金石是古人铭刻功绩的素材。钟和鼎是古代青铜器中体积最大的,可以铸刻较长篇的铭文,因此就用“钟鼎”来代表一切青铜器。但这个词现在不用了,一般已改称为彝器。钟鼎上铸刻的文字,其内容大多是记述功绩的,字体都是小篆以前的大篆,,或称籀书。这种文字,从前称为钟鼎文,现在称为金文。(《“金石”、“文物”、“考古”的各自含义》)
大约在西汉晚期,有人开始在石板上刻上文字,记述墓中人的姓名官位,卒葬年月,放在目前。这个东西称作墓表……以后石板上刻的文辞渐渐多起来,详细地记述了墓主的姓名、家世、生平和事业,还加上写颂扬和悼念的诗铭。这样就成为一篇传记,使过路人读了,可详细知道墓主人是何等人物。这块石板,就成为墓碑。(《说碑》)这么看来,年年清明上坟,先人墓前立的那块刻有谁于何年卒葬,子孙人等所立的石板不是墓碑,而是墓表了。
汉碑《北海相景君铭》有“竖建虎口(上非下石)”一句,这个字(上非下石)从宋代的洪适到清代的翟云升、翁方纲,都不识得,所有的字典里也都不收。(《说碑》)汉字知多少。
清代中叶,包世臣作《艺舟双楫》,竭力提倡书家要多临碑,少临帖。他以为碑字多篆隶真楷,有端庄刚健之气;帖字多行草,气骨柔弱。学习书法,应当从临碑入门,大好刚健的基础,然后学习行草书,不致柔媚无骨。他以为碑都是中原古刻,特别重视北魏碑的书法,因此他以碑字代表北派书法,帖大多是南朝文人的字迹,他就以帖字来代表南派书法。北碑南帖,成为书法艺术的一个新词,于是碑帖二字,又产生了新的意义。我们说某人是临碑的,这就是说他写的是篆隶真楷;如果说某人是临帖的,这就是说他写的是行草书。(《说帖》)
金石学奠基于宋代,欧阳修应该被归功于金石学的创始人。元明二代,比较冷落。石刻碑版方面,还有些人,金文方面,却是人才寥落。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学者不易见到实物,也无拓本传世,不能取得研究资料。清代是金石学的大盛时期。古物出土,时有所闻,而且每一件古器物都有拓本流传,更有不少古器,有全形摹拓,即使未见实物的学者,也能据拓本进行研究。(《先秦金文》)
唐代几乎所有书籍都是手写本。有一些没有取得功名的读书人靠抄书卖钱过活。他们抄的大多是儒、释、道三教经典,故成为“经生”。一般的经生,书法都还不坏,如果写得不好,也没有人买他的写本了。(《唐墓志、塔铭、经幢》)
施蛰存《金石丛话》,14篇文章从14个专题梳理金石学基础知识,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文库典藏本”之一种,硬面精装,2013年4月1版1印。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不少。可惜作者名给弄错了,应是“施蛰存”,而不是“施蜇存”。总阅读量第1589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