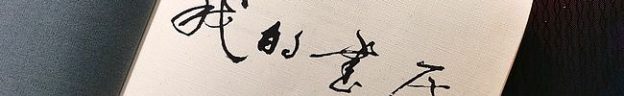太座给二娃喂奶时,从沙发靠垫后面抽出一本“读库”,翻开至夹了书签的地方继续读。女儿已经读完“哈利·波特”系列的前四本共一百多万字,蜷在沙发一角在读第五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我读完第二遍徐贲的《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在整理旁批、眉批和重读一些划了线的关键句子和段落。客厅里,伴随二娃吃奶、翻书、写字、敲键盘声音的,就只有小田和正的歌声。
上个月,我和女儿把客厅布置成了第二个书房,一面墙的书架上,是近一千本从我的书房和女儿房间的书架上搬来的书。我觉得,不能因为女儿才四年级就只给她对应程度的书,应该让书架上可供阅读的文本要有足够的多样性。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他不知道的,了解他不了解的,阅读文本的多样性不但可以尽可能摆脱某一本、某一类书籍和思想的局限,还能够“从多样性的阅读经验得出对一些常见‘人文问题’的普遍概念(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为何受苦、人死后会如何、人为何会对某些事情感到惊诧和敬畏),这是一种必须由每个人自己来归纳、总结的思考,也需要结合个人的人生观察和体会,在尽可能广泛的知识范围内,多角度的反思。”(P.25)“尤其是在知识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的互联网时代,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P.8)因此客厅书房书架上的书除了漫画、戏剧、历史、小说,还有宗教经典、哲学对话、诗歌以及科学等种类的图书。但女儿最喜欢的书不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亨利·哈格德的《所罗门王的宝藏》、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网格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或精装珍藏版《科学的旅程》,而是一本我从旧书店淘回来的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五月一版一印《常用成语故事选》。她几乎每天都会抽出这本正体(繁体)字的书随便翻看两页又插回去,“我喜欢这种书,翻起来好像字都是活的,在动,这种已经变黄的书页让我感觉很舒服,家里有这些‘古老’的书真的很幸福。”她说。或许这就是人文知识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根本特征之一——“绝对新的人文知识是几乎不存在的。人文学科不能不,也必须不断地回到那些古人已经在讨论的基本人文问题上来: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理性和信仰?”(P.406)
现在,我们的客厅书房书架上,书的种类和数量依然每周都在增加。明天(年三十)新增的将是两本地图册,一本中国的,一本世界的,这也是给女儿的新年礼物。大前天晚上,女儿给我们看了她的梦想笔记本。在她的梦想计划里,要先去甘肃莫高窟、浙江杭州钱塘江、安徽黄山、四川九寨沟和黑龙江哈尔滨旅行,然后去美国、英国学习,目标是要成为一名“游戏家”。她在每天的“王者荣耀”时间后,要制定旅行计划和预算,需要最新版本的地图。虽然这些地图在互联网上就能看到,但她仍然想拥有纸质版的“真正的地图”。我们还讨论了如何像博多·舍费尔的《小狗钱钱》里12岁女孩吉娅那样去赚钱和理财,早日实现梦想。现在女儿已用学到的语文、数学、自然科学、艺术等学科的知识,为还不到五个月大的弟弟创作了三本毛边小绘本和一本立体书。陪伴女儿的这个过程,给我下个学期四、五年级阅读和写作课程的教学,提供了一些可能有用的方法。
在我看来,幸福学堂的阅读和写作课,其实就是人文教育,就是如施特劳斯所说的:“人文教育是一种读写教育,一种用文字和通过文字的教育。”(P.208)“人文教育以阅读和讨论为本,目的是培养人的思考、提问、讨论、表述的能力——这些是包含在‘阅读’的知识范围之内,而不是外在于阅读的。所以可以说,人文教育是一门离不开‘阅读能力’的课程。”(P.23)但这门课并没有像语文、数学、社会科学那样的“国家标准”教材,课标的要求也很宽泛,我在为人文教育选择课本时,“一个重要的考量便是让学生们能在最大程度上将阅读与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进行联系,而这种联系最重要的枢纽便是人类普遍面临的伦理和价值问题。”(P.96)于是我将从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选出十二部,和学生一起完成阅读、理解、分析、仿写和创作。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由美国图书馆儿童服务学会创设于一九二二年,每年颁发一次,以奖励上一年度出版的世界范围内的英语儿童文学优秀作品。这些获奖作品题材涵盖了自然、亲情、友情、探险,甚至战争,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门课对阅读文本多样性的要求。
“美国19世纪废奴运动领袖、人道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说过,‘你一旦开始阅读,也就会永远自由。’”(P.128)“没有思想的自由便不可能有自由的学术,也不可能有自由的教育,而人文教育则尤其离不开自由。”(P.388)“这世界上有不同的奴役,也有不同的自由,但是,借助独立思考和判断的阅读来摆脱奴役的路却是一样的。精神自由、意识自由、思想自由的道路都可以由这样的阅读来开启,作为自由教育的人文教育,它的经典阅读要起的正是与此类似的作用。”(P.128)
“人文教育的全部活动,至少是最主要的活动乃是把价值问题重新置于知识学习的中心位置,并以此使得知识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虽不一定是智慧,但却随时都在亲近智慧和摆脱愚蠢的智识。”(P.14)“知识不等于智识,这并非在互联网时代才如此,但却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突出。”(P.9)
“智慧的对立面是愚蠢,知识的对立面是无知。学习知识可以改变无知,但却不一定能改变智慧。人文的智识学习目标之一便是识别知识与智慧,并通过这种识别,尽量对愚蠢保持警惕,尤其是在碰到知识或权威人士的愚蠢时。”(P.11)因此,“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最需要学习的是有积极价值导向和批判问题意识的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获取被叫做‘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唾手可及的现成信息。以培养这种能力为宗旨的人文教育因此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专业教育可以让人知道‘是什么’和‘怎么做’,而人文教育则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和‘为什么’。唯有此,学习才能从‘求知识’提升到更有意义和更高一层的‘求智识’。”(P.7)人文教育也才有可能达成根本目标——“人的心智的解放和成长。”(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