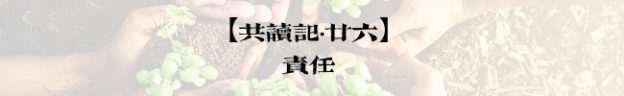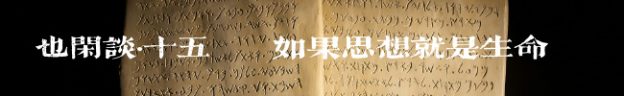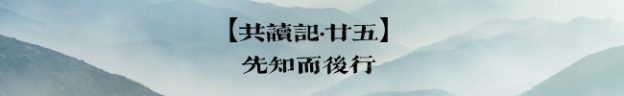今天的热身写作,将学者分为两组,每人一张写作题的纸条,不需要讨论,三分钟思考,五分钟写作。时间一到,不论写作是否完成都要停笔,然后分享。写作要求是观点的公共表达,也即是这个问题和讨论不是给某一个体的,而应是关乎这个小小星球上的每个人类个体的。
一组的题是:今晚你要与一位来访的国家领导人共进晚餐。就餐时,你们将讨论一个问题,并阐述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是( )你的看法是( )。
另一组的题是:你是一位来自某香蕉共和国的国家元首。今晚,你要与这个国家的一位陌生人共进晚餐。晚餐时,你们将就一个当下热门的话题展开讨论。这个话题是( )你的观点是( )。
高小班的学者与初中班的学者提出的问题,有着极大的年龄和思考程度的差异。
高小班学者的问题,大多关于生活或看似充满想象力但其实不着边际。他们应该还不明白题中这样的身份和对话意味着什么。下次题的难度要调整。
初中班学者的话题有关于种族歧视的,有关于俄乌战争的,有关于战争的正义性的。这些话题单独出来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也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在一次讲谈中探讨清楚其中的任何一个。这个环节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每位学者都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并能够建构自己的思想,明白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而不是在封闭的学校里学习的那些已经被AI掌握并不断更新的,但仍然陈旧的为了考试而学习的知识。“如果思想是生命,是呼吸,是力量,那么思想的缺乏就等于死亡。”([英]威廉·布莱克《苍蝇》)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应该是要有思考、有思想、有力量的独特个体。
《千字文》讲了四句: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再次通过这个文本告诉各位学者,不要低看了这里面的内容。仅这四句,就包含了七八年级地理和历史的课本知识,而这是一千多年前的“儿童启蒙读物”。所以,当下的教育,到底是在进步、原地踏步还是退步?
金生丽水:长江这条世界第三长河的上游金沙江、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的川江、湖北宜昌至江西鄱阳湖的中游,鄱阳湖至南京的下游,以及南京至出海口的扬子江。外国人了解长江,始于扬子江,所以长江的英文是Yangtze River。
玉出昆冈:在白板上画出阿尔泰山、天上、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这中国西部四大山脉,再在其中定位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以及青藏高原。讲白板上的示意图移到墙上的巨幅中国地图上,地理位置一目了然。现代人提到玉,首先想到的就是和田玉,而新疆的和田就在昆仑山北麓。在古代,只要是美丽的石头,都被称作玉,所以有很多斜玉旁的字。
剑号巨阙:越五剑,欧冶子所铸。五剑各有不同。胜邪,残剑,因邪气太盛而没有最终铸造完成;湛庐,钝剑;纯钧,佩剑;巨阙,号为“天下至尊”之剑,可能是一把双手剑,在春秋时算是一把巨剑;鱼肠留在最后讲,这是短剑,刺客之剑,得名于一位刺客将之藏于鱼肚子里,借机靠近防卫森严的目标并一举完成刺杀任务。有学者从刺客想到荆轲的图穷匕见,并问这位鱼肠刺客的名字,还有学者说《长安十二时辰》里的一位刺客就名叫鱼肠,我说当讲到《刺客列传》时,这几位刺客的故事,我们都会一一道来。“又埋种子啊!”学者说。“不然呢?”
珠称夜光:从中国第一部志怪小说《搜神记》里,随侯珠的故事说起,延伸到语文课本七年级《狼》出自《聊斋志异》,而“聊斋”是蒲松龄书房的斋号;《河中石兽》一篇课文选自《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而我曾亲见竟有语文老师严肃认真验证其科学性,真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上午的高小班,《史记·夏本纪》推进到“陂九泽,度九山”。重点仍然放在了《夏本纪》里禹为了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与历史书上禹治水十多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对比分析。
下午初中班,《夏本纪》“帝锡禹玄圭”,讲了“璧”、“圭”、“璋”的形状和用途的不同,重点放在“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再次,“佐禹日浅”不过是个借口。因为从前文本可知,在禹开始治水时“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此时益就是禹的副手。治水十三年功成于天下。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这算下来,益辅佐禹四十六年,怎么说也不至于“日浅”。结束了主题四,进入主题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摩西、海伦和妲己”。主题五由局座秋蚂蚱来从摩西开篇,今天一个小时下来,似乎他只讲了准备内容的三分之一,而后续还需要他继续的是《伊利亚特》的特洛伊战争。我有点担心他如何讲这个让整个希腊城邦的国王们都为之迷倒的宙斯的美丽女儿,在与特洛伊王子私奔后引发的浪漫背后,还夹杂着诸神的嫉妒的战争。
其间有书店的顾客推门进来,问:“这是书店的课程?”
我说是的,这是针对中小学生的人文通识课程。
他问:“每个周六都有?”
“是的,每个周六都有。上午是小学班,下午是初中班。”
看了讲义后,他好奇:“你们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课?每次都是这样对书店的顾客开放的?”
“开这个课,是源于我们希望提供教育的另一种可能,这也是我们认为的社会责任。每一次都是公开课,欢迎推门而入,每一次都是现场直播,没有表演,真实呈现。”
“什么时候开面对成人的课程?”
“这个你得一会儿结束后问正在讲课的这位书局主理人了。”我笑说:“那应该是他将在2025年启动的课程。”
一天的讲谈结束,有学者读完了两周前推荐给他的龙应台的《野火集》,觉得打开了看问题的新角度,向家长请了专款,让我再推荐几本。乔治·奥威尔《1984》、《动物农场》;扎米亚京《我们》、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刘瑜《观念的水位》。“这一溜下来,你的预算应该就差不多了”我说。结账时,书店给他优惠,开了会员,折扣下来还有预算,于是又捎上了周濂《正义的可能》和特价的柴静《看见》。“哈哈哈,这个寒假就充实了!”他大笑,忘了这是在书店,应该要安静,应该要“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