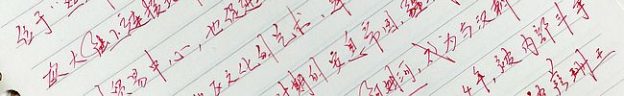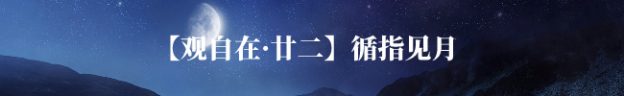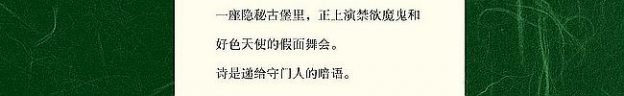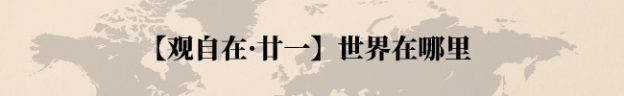打乒乓球时,学生X君来到我的面前,“豆总有空吗?我想和你聊聊。”我说好啊。坐在台阶上,她说了游学给她带来的困扰,想听听我的建议。
“我明白了,在游学这件事上,有的发起人是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的特种兵,有的是综合能力还不错的将军,而你的困扰来自你是一名被迫做了将军的特种兵。游学要求大家跨年级组队,作为发起人的你就必须面对成员能力参差不齐和态度各异这个现实问题。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你的团队管理能力。首先,成员的加入方式是什么?”
“我有发起招募和面试。”X君说。
“招募和面试就是准入机制,那就应该有退出机制。退出机制不是惩罚,而应是一个大家商定的自然后果,就像开关按下去灯就会亮起来这么简单,这就是规则。规则就是你们游学组内约束每个人的法律。你不能在一个团队中指望靠道德来团结所有人去达成目标,因为道德只能用来律己,规则才能律人。”
“那我现在还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有的成员他不参加团队的讨论,也不接受任务,更不去完成,因为他觉得只要是在一个游学组里,就算什么都不做也是能够去游学的。这就导致这个游学组虽然看起来人不少,但根据分工每个人要完成的任务都不能完成,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在做。这让我感觉很累,很痛苦,这样的游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邀请学生沈加入吗?交给他的任务不但能完成,而且非常有学术性,他就是那种你能放心托付的可靠的人。”
“他哦,还给我布置作业来的,刚完成了他的安息帝国作业。不过我也给他准备了彩蛋,关于‘图兰朵’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哈哈。我这个学期没上游学课,所以不清楚你们现在的规则是什么。但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要有退出机制这个自然后果。有后果就要有KPI。KPI的设置是在大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督促团队中的每个人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指定的任务,共同推动项目的进展,从而实现‘游学’的共同目标。‘去游学’就是大家的共识和目标。要达成大目标,就要将任务分解到每一个人头上,用目标管理的方法,准确告知每一个成员他领到的任务要求、完成标准和截止时间,并明确时间三分之一、一半和截止前一天三个任务进度通报时间节点。每个成员的任务难度是根据他的实际能力设置的。你要在每一个时间节点清晰、准确知道任务是否完成匹配的程度。”
“你和沈真的是已经进入可以开展学术对话的程度了。可是我还面临团队里有人摆烂、不参加、不配合,我要怎么办啊!?”
“当你发现有人不参加、不配合、不沟通、不完成,你需要和他沟通,了解是能力问题——任务的设置超出了他的能力而无法完成,还是态度问题。”
“如果是能力问题呢?”
“每个人都有能力不足的时候。作为领导者,你第一需要调整任务的难度和要求,以匹配他的能力,并借任务提升他的能力;第二需要将他不能完成的那部分任务内容拆分给其他还有余力的成员。”
“如果其他人都没办法承担这部分突然多出来的任务呢?”
“别忘了,你不但是这个项目的领导者,你还是团队里单兵作战能力最强的特种兵。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就是那个遇强愈强的人。这,就是所谓领导力——担当、沟通、协调、判断、整合。”
“如果他是态度问题呢?”
“启动退出机制,然后反思你对准入机制的把控。”
“那离开游学组的那些人如果不能去游学怎么办?”
“那不是你现阶段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事。这超出了你的能力和责任范围。”
“谁来面对和解决呢?”
“游学课老师。”
“好。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