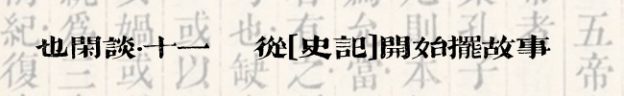什么是历史?今天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有的学者很快说出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有的表示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现在就是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说。
一轮下来,各位学者对历史的理解和定义碎片,算是基本拼凑出了历史所包含的要素,从而引出局座大人秋蚂蚱携“中国历史的记录与篡改:信史是如何消亡的”话题登场。上午小学生场,局座讲的是“崔杼弑其君”,因为在学校,七年级才开设历史学科;下午初中生场,局座讲的五四运动。
上午我从局座大人“崔杼弑其君”的“杼”接棒,引出“札扎弄机杼”,给“古诗十九首”埋了一颗种子后,就开始了《史记·五帝本纪》。《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写的就不是信史,而是神话。“话”就是故事的意思,神话就是关于神的故事——如果想被人记住,首先得要有一个好故事,给四五年级的学者讲《史记》,其实就是在讲故事。
五帝之前是三皇,在白板上写下“皇”和“帝”的甲骨文,但没有说是什么字,于是诸位学者就此展开了想象力各种解读,公布可能的答案,一个是熊熊燃烧的火把,一个是正在点火的人,也就是一个掌握了火的使用和分配,一个掌握了用火的能力,或者可以说皇和帝是一个部族里掌握了火这种当时最“高科技”的人。就此开始《五帝本纪》一人一句,先读再说,要求不管是否正确,一定要思考并说出自己的理解,然后我再一字一句,逐字逐句说出我的理解,因为如“神灵”、“徇齐”、“敦敏”、“聪明”,一个字就是一个词甚至一句话。有学者猜“敦”应该指的是一个人很有钱,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请让我狠狠敦一些吧,这样我就可以把整个也闲书局的书都买下来了,简直不要太快乐。如此古今义对比下来,只讲到“神农氏弗能征”。
“我们这半天就讲了四句啊?”结束时有学者提出疑问。我说:“这很正常啊,后续甚至会一次讲下来就只讲了一个字嘞!”
下午,局座大人借“五四运动”讲了教科书与史料内容的不同,结束时,我保留了白板上“傅斯年”、“罗家伦”、“乌合之众”等几个关键词。从“傅斯年”,给各学者讲了一个故事:
一位北大学生,黄昏时分,打北河沿走回沙滩。一辆汽车飞也似的从身边驶过,溅了他一裤泥水点子。心里立即充满着焰腾腾的怒火,一直到宿舍仍未有半分减弱。一走进宿舍门,他就大声地对正在埋首伏案的两位同学嚷着:“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这晚他们都没怎么睡,几个人从贫富的悬殊谈到阶级的分化,以及国家是如何被“汽车阶级”所败坏。隔日,咒骂汽车的人把这些思考和讨论的结果写成了一篇札记,发表在北大学生自办的一个刊物上。文章里,他再次重复着那句充满怒气的话:“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刊物名字,叫《新潮》。文章作者的名字,叫傅斯年。
“傅斯年在上大学时,也是妥妥一愤青呐。这个故事我从哪里看来的呢?杨早的《说史记》。也闲书局有杨早的《说史记》、《野史记》和《民国了》三本书,都是民国的故事。一本好书或一篇好的文章,要么是讲了好故事,要么是讲好了故事。还有《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本书,也闲也有,一本我觉得每个人起码要读一两遍的好书。”
“你的植入广告要不要这么直接?”有学者说。
“在书局讲谈,提到书不就应该这么简单粗暴么?”
跨越五千年回到《五帝本纪》,一人一句,讲到帝喾,有学者提醒:“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今天的结束时间已经在15分钟前就到了。”
“继续嘛继续吧。”几位学者说。
这时书局的活动区域正在举办戴明贤老先生的新书推荐活动,为避免互相干扰,我还是就此打住。
结束后,与一位专程来蹭课和叙旧的学生在书局门口聊了半小时。想听听戴老的分享再回家,但人太多,挤不进去,不愧是顶流。离开书局时买书一本,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系列39种之一,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