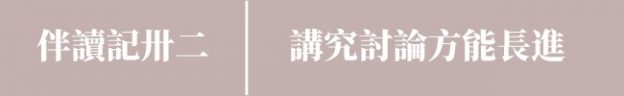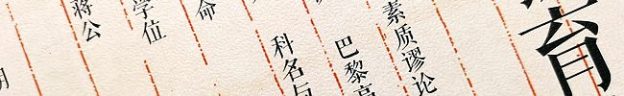花卷终于基本康复,自学课也恢复正常。
今夜,课程内容推进到了李白。复习了《静夜思》、《赠汪伦》、《望庐山瀑布》、《夜宿山寺》、《独坐敬亭山》、《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八首,顺带说了《静夜思》的两个版本。
李白的《静夜思》,在乾隆时人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也是选入教材时的版本。但在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卷六)中,为“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清版与宋版有两字不同,孰优孰劣不论,后世改动的也已不是李白的《静夜思》,人也不知原诗样了。所以后人读唐诗,总是希望得到宋版集子作为依据,这是因为除唐写本外,宋本已是最近原貌。宋本不可得,则求明复宋本或影钞宋本,只为求真。
复习了诗,我们开始互相就“香菱学诗”向对方提出问题,讨论文本,正如黛玉说的:“正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
最后花卷计算了“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这一段里,黛玉对香菱学诗所要求的基础诗词量大概在500首。
“爸爸,500首古诗词这个难度太大啦!”花卷说。
“看总量是有点吓人,但你把这个目标分解到一年中的每一天试试。按照我们现在的进度,完整的一年下来,你就有这个基础量了。”我说。
且说香菱见过众人之后,吃过晚饭,宝钗等都往贾母处去了,自己便往潇湘馆中来。此时黛玉已好了大半,见香菱也进园来住,自是欢喜。香菱因笑道:“我这一进来了,也得了空儿,好歹教给我作诗,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作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香菱笑道:“果然这样,我就拜你作师。你可不许腻烦的。”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香菱听了,笑道:“既这样,好姑娘,你就把这书给我拿出来,我带回去夜里念几首也是好的。”黛玉听说,便命紫娟将王右丞的五言律拿来,递与香菱,又道:“你只看有红圈的都是我选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问你姑娘,或者遇见我,我讲与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诗,回至蘅芜苑中,诸事不顾,只向灯下一首一首的读起来。宝钗连催他数次睡觉,他也不睡。宝钗见他这般苦心,只得随他去了。
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见香菱笑吟吟的送了书来,又要换杜律。黛玉笑道:“共记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红圈选的我尽读了。”黛玉道:“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香菱笑道:“领略了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说与你听听。”黛玉笑道:“正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你且说来我听。”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