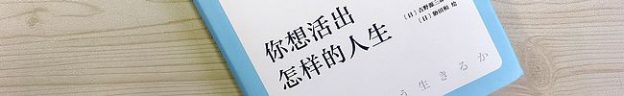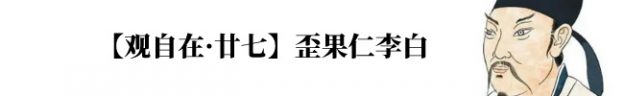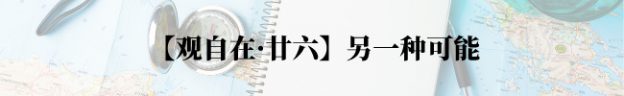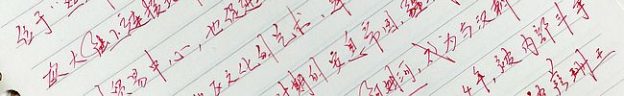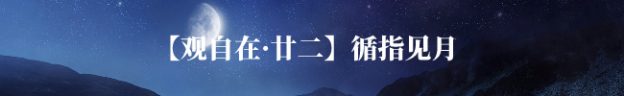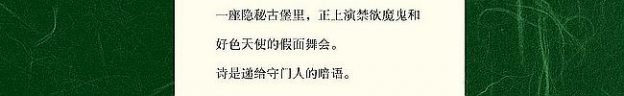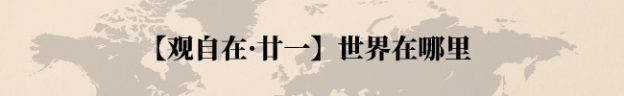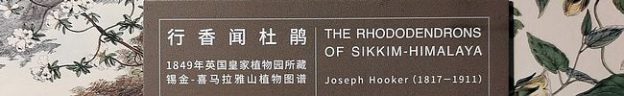语文课,今天将王维的主题收了尾,明天合班开始李白的新主题。
上周从2班申请转班来的八年级同学林,一周下来融入得不错,渐渐不再拘束,课堂上开始与我有对话,课后会来找我讨论她每天的常规作业“每日一记”小说连载的情节推动,几好的。周末三天的“每日一记”和课题作业,“一次性拿到三个‘A’,你是我上这门课来的第一人。”我在作业后留言。
本周从2班申请转班来的六年级同学白,融入得更快,确切说只花了半节课就进入了课堂,参与互动并能提出问题,几好的。对他每天作业的要求是“多描述,少感慨,一句一句写清楚。”
花卷和同学吴一向是活跃分子,听得认真互动积极,并常常抱怨我讲得太快来不及记笔记,然而她们的教材上密密麻麻都记满了笔记。
六年级的同学张已经和同学林连载创作复线小说《小棉故事》一周了,她在同学林的故事里是第一季的终极BOSS大魔王张一一,在她的故事里,同学林是小棉的守护者。在她们的小说里,同学林的妹妹小棉是一个像噬元兽一样,可以吞下从天而降的陨石的可爱小女孩。没有什么写作比写作者自己要写更棒的。每天读她们的作业,就像在追剧。我只需要做一枚观众就好了——在作业后的留言就像是在写影评。
同学曾最近在课上跟随不佳,不是走神就是瞌睡,在作业本上留言提醒了几次,也请导师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在课题作业里,他写“那些急于赶路的商人,他们追求财富急功近利,然而欲速则不达,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留言:“今天的作业,请回答我两个问题:1、追求财富有错吗?为什么?2、急于赶路就是急功近利吗?为什么?”
被大家称作“地理天才”的同学邹,虽然读和写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障碍和挑战,但他将地理当做了图形游戏,什么样的图形和颜色代表什么地形,每一个地点都在图形的某一部分,并在另外一些部分的东南西北方位,以及结合听和交流学习历史——这些地点背后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它们之间又是怎样的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学习方式和对外界的认知,并长期保持在课堂上的活跃。每当有人回答不上我提出的关于地理的任何问题,他们都会说:“请‘地理天才’来帮我回答吧。”这时候同学邹就会带着得意又腼腆的表情走到地图前开始他的专属环节。
被大家称作“历史天才”的同学沈不知什么原因大半节课都不在状态,还好在下课前两分钟的“飞花令”环节参与了进来。课后交上来的作业里,没有课题作业,也没有每日一记。我留言让他补来,并要求对未按要求完成作业给我一个说明。他拿到作业后,笑嘻嘻来找我,说:“好嘛,我补来嘛。”我想,他或许只是在试探自己是否一直被“看到”被关注到。
本周值日,没有参加飞盘课。下午四点,在从停车场进入校园的通道口值班,两位家长与学生导师第一个六周面谈后准备离开,看到我就断断续续聊了大半个小时。大意似觉得我在学生的六周评语里表达的鼓励和赞赏不够,只是在陈述事实,这可能不利于化解该学生与我之间的隔阂。对前半部分,我接受,以后会更多鼓励;对后半部分,我表示并不知道,也没有感受到有明显的隔阂,于是我们就开始探讨和猜测这个隔阂产生的可能原因。在关于师生关系的探讨里,家长提到学生还是比较看重老师的认可,因为之前在公立学校读书,老师被树立为绝对权威。“可是我觉得学生不需要将老师是否认可看得那么重要,老师不是拿来让学生听从的,而应该是学生对话的对象。老师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另一种可能——可能我们都是对的,也可能我们都是错的,因为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就像1+1=3这个错误不能证明2+2=6是正确的一样。我常常在课堂上说‘你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非常好,虽然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说出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比赢得别人的赞同更重要。’”
这个学期,我仍然不担任任何学生的导师。但从几年前第一次担任导师起,每周都会固定某一天下午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用于与上我课的学生的家长面谈,回答家长关于课程、作业、学生状态、教学思路等等任何关于教学的问题。但,就像学生一样,会主动来提出问题、交流探讨者总是可遇不可求。明天下午四点要见的家长,是这个学期第一位主动想“从老师的角度认识一下自己的孩子并了解一下老师”的家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