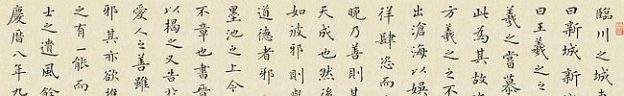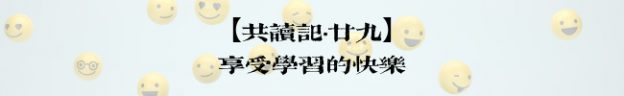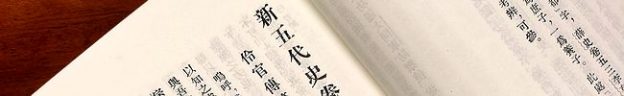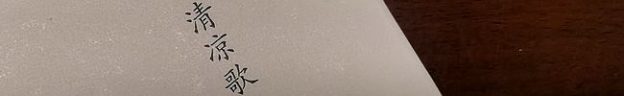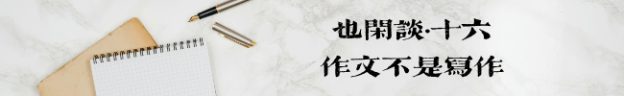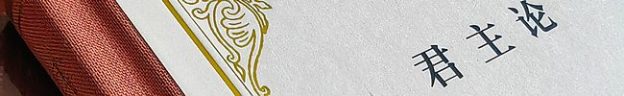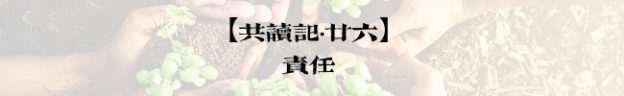冬至,我们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因为……“关于南北回归线”,学者说。完美,太阳直射点抵达南回归线,北半球最黑暗的一天,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准备过圣诞节,北极圈内是太阳总也升不起来的极夜;而南半球的人们在暖洋洋里迎来圣诞,南极圈内则是太阳在地平线上徘徊却总也掉不下去的极昼。这就是世界,同一时刻的不同。不同的人,看到的同一个世界是不同的。
随堂写作,上午的高小班主打有趣,下午的初中班试图提出问题。
高小班三个题——
给女生的题:我是赵铁柱。我刚失忆了。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给男生的题:茶店村最漂亮的小芳妹我昨天成功发明了一种能够一次性画出五颜六色的黑的画笔。现在我必须要写一段话来向英文名为Here We Go的村长黑尾狗,也即是我的意向投资人介绍这个发明以争取她的天使轮。我的这段话是这样的——
给最活跃者的题:给一碗陈二嬢老贵阳素粉写一份悼词,并一边朗读这份悼词一边吃掉它。
诸位学者拿到题,“啊?!这是什么题?!”老规矩,不可以讨论,三分钟思考,五分钟写作。时间一到就停笔,并分享写下的内容。分享时间,先是题一读出,就笑倒一片,“毛豆,你是来搞笑的吗?”
“我是认真的哦。”等诸位学者分享完,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位女生的名字会是‘赵铁柱’?一个失忆的人怎样认识自己、介绍自己?如何悼念一碗老素粉?这就是要打破,打破固有思维。因为如果停留在固有思维里,认知和表达就会僵化,就会套路,没了活力。写作文不是写作,所以才叫‘作文’,就是作一篇文。写作要求一个人的思维,必须要活跃、好奇和充满想象,不被套路所套路。”
冬至,好多地方有吃狗肉的习俗,请诸位说说自己吃不吃狗肉以及原因。一圈下来,我问:“每当这个时候,爱狗人士们就会说‘狗狗好可爱,是人类的朋友,你们怎么忍心吃?’那羊羊和猪猪做错了什么就要被吃掉呢?并且中国人吃狗肉的历史可算是悠久。《晏子春秋》载,齐景公的‘走狗’(猎狗)死了,要用棺敛之。晏婴提了意见,于是景公请臣子们吃了一顿狗肉宴。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事,只是选择,没有对错,更不需要道德绑架。”
千字文,讲了“果珍李柰,菜重芥姜。海咸河淡,鳞潜羽翔。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仓颉和嫘祖,有学者知道,于是他们来讲,我的重点放在“裳(音长)”。
“《诗经》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没学过。”
“好,没关系,我们会有一个主题讲《诗经》。”
“‘云想衣裳花想容’?”
“没学过,不知道。”
“没关系,到唐朝时我们会讲到。今天冬至,我们有毛衣、棉衣、羽绒服穿,好暖和。可中国人在南宋到元朝时才有棉衣穿,宋以前的人过冬穿什么?”薅羊毛搓绳做的毛衣、皮衣、有乱麻作为填充物的夹衣,直到家住在山上,每周六进城一趟来也闲书局上他唯一的课的学者说自己昨天杀了两只鸭子,鸭绒可以自己做羽绒服。妥妥的一部极简中国冬衣史。
一位学者说冬天取暖还可以喝酒,多好,我说:“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好冷,如果晚上下雪的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首诗……”
“我不知道这首诗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生活好享受。”山上来的学者说。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诗词就是生活。”我简直太享受了,嘴一滑就滑到刘十九和刘二十八去了。会生活的人,才能领会诗词的妙,而不是因为考试要考。为了考试而学古诗词,是花下晒裈、焚琴煮鹤,大煞风景且不得其乐趣所在。上午原计划结束《夏本纪》,因为嘴滑,进度没完成,留了个尾巴。要不要检讨?不检讨。
下午初中班,因为局座秋蚂蚱要主持书局三点的活动,所以他接着上周的内容,继续讲摩西。半小时讲完《出埃及记》,我接下来借《十诫》说,各个宗教都有不杀人、不偷盗、不做伪证(不说谎)之类的戒律,并且都有“神爱世人”这类似的爱的福音,如果神真的爱世人,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几千年来有那么多因宗教引发的战争?从大卫六芒星开始,公元前1000年古以色列联合王国建立后就被两河和地中海崛起的亚述、巴比伦、波斯、古希腊、罗马所轮番征服。终于,在公元70年,犹太人灭国,被罗马人赶出巴勒斯坦地区,开始长达2000年的流亡,直到1948年以色列的建立,定都特拉维夫。1980年,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不可分割的首都”。1988年,巴勒斯坦通过《独立宣言》,也定都耶路撒冷,从此这个城市同时成为了两个国家的首都。在这个城市的老城区,有犹太教的圣地哭墙,有伊斯兰教圣地圆顶清真寺,穆斯林相信寺中那块石头就是默罕默德随大天使加百列升天看到天启之处;还有基督教圣地,耶稣坟墓所在地的圣墓教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可以视为犹太教的“两个儿子”,这“一家人”的这么多圣地集中在一起,对哪个宗教来说这里都是神圣不可分割的,怎么办?!在这些纷争中,随着2007年哈马斯的占领,加沙地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以色列人围绕着这个大概只比南明、云岩两城区略大,或者只有一个花溪区大的狭长地带,修建了70公里长的围墙,墙上架设了机枪,将里面与贵阳两城区常住人口相当的两百多万人困在里面,他们缺水断电缺食物,更多时候只能靠人道主义救援。如果神爱世人,什么神爱的是什么世人?所以耶路撒冷三千年的纷争,可能还要延续三千年。
公元70年,犹太人开始流亡。这一年是东汉明帝十三年。前一年,明帝夜梦金人飞升而至,于是派人西行求法,摄摩腾和竺法兰的白马驮着经书向东而来,中土第一座官办佛寺由此得名,“白马东来”将是我们讲到东汉时的一个主题。由此结束上半段。
下半段,随堂写作需要诸位学者使用手机借助AI完成。题为——
今天是你在这个城市生活的第十年的最后一天,你曾与希帕科斯(Hipparchus)在这里成为密友,而今他回到尼西亚已五年。明天,当第一缕晨光照射在也闲书局门前的狗尾巴草尖上时,口服毕一碗肠旺面的你将启程去见被诅咒的阿尔刻迈翁家族成员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告诉他这十年苦苦思索的答案——( )法并不能保证公民对官员优劣的评判都是深思熟虑和准确的,为了保证像你这样与大多数人持不同观点的少数能够得到平等、尊重的对待,而不是被淹没、被无视,这个法案就必须要做出如下修改( )。
十分钟下来学者们发现,自己每一个字都认识,但却不知道这段文字想让自己做什么,AI也不知道。所以,这成为每位学者今天的附加作业。
“豆总,这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学者问。
“这就是一道阅读理解题。现在AI最擅长的是回答问题。如果你不能给它一个明确的问题,它就没有办法给你回应。而现在人与AI最大的不同就是,人能够发现和提出问题。我想通过这个题引起各位思考:AI知道的,人类就知道吗?人类如果借助AI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是否意味着这是一种无效的学习——因为只是知道了知道的。什么是学习?什么是知识?如果一位学者提不出问题,这将是最大的问题。”由此我们就这道题中的信息和关键词展开了讨论。
讨论告一段落,准备开始《史记·殷本纪》,“豆总,只剩下八分钟了。”
“时间这么快的吗?好吧,这个主题的重点不只是殷商和妲己,除了摩西,还有宙斯这个花心大萝卜与凡间女子所生的女儿海伦的私奔引起的地中海世界大战。我们下次快速过掉比较简单的《殷本纪》,好好唠唠特洛伊。”
今天,小糜老师为大家准备了两份礼物,圣诞盲盒和各位学者自己名下的也闲书局会员卡,马上是新的一年,每次讲谈不但要有新知,还要开心。
一天的讲谈结束,带着一只耳朵,隔着一堵书墙,蹭也闲的新书《阿包》推介会。交流环节,一位新加坡的贵阳人说,要将阿包和《阿包》这种本土的写作介绍到南洋,让我想起黎紫书的《流俗地》。刘临洪教授买了一本《阿包》并现场排队请作者阿包和潘年英签名后送给我。最爱签名本。可惜忘了请刘临洪教授也签赠。
离店购书一本,弘一大师《清凉歌集》,中国画报出版社2017年1版1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