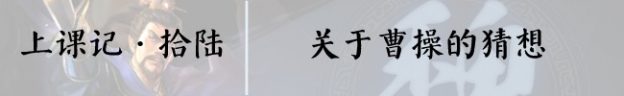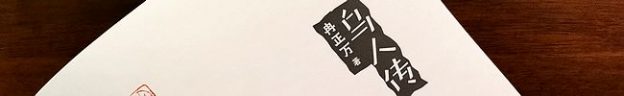喉咙痛。一天都在含咽立爽口含滴丸。
【语文3班】
连堂,讲了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曹植的《梁甫行》和刘祯的《赠从弟·其二》。顺利完成主题二十五:建安风骨之三曹七子。下周开始主题二十六:魏晋风度之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八年级历史】
复习八年级内容。下课前与学生讨论,下学期历史课是从七年级上册开始复习,还是直接进入九年级世界史内容。讨论下来,学生希望回头从七上开始再快速跑一遍。
【七年级历史】
测评七年级上册内容。下课前对学生说,测评不是为了统考你们能考出高分。不论历史还是地理,甚至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应用题,其实都是阅读理解。只是在历史课时段,我们选取历史素材来作为阅读理解材料。
【学部会议】
每周四下午4点学部例会。这次我提出了四个议题。
这几年,我在训练自己遇到或要去做一件事情,先跳出这件事和这个场域来看,来提出问题。回答得了这些问题,我认为就是“说得清楚”,可以一试;不做也不参与“说不清楚”的事。所以每个“黑色星期二”的备忘是“金刚手段,菩萨心肠”。提醒自己,没有菩萨的心肠,就不要去行金刚的手段,否则伤人伤己。周四的备忘是“临事静对猛虎,事了闲看落花”。事来如虎,人来亦如虎,时也势也。周五的备忘是“满地江湖吾尚在”。周六是新增的一句“一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周日的备忘是“一个人牵挂自己的念头多寡,多少能见证他的实在修行”。提醒自己一个观点、一个看法,后面都是一个人,是人就会有偏见,有私心。《聊斋志异》开篇即言“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